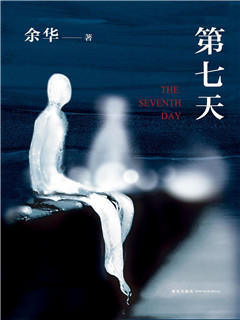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AA+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
简
第五天
2018-10-2 18:51
我尋找我的父親,在這裏,在骨骼的人群裏。我有壹個奇妙的感覺,這裏有他的痕跡,雖然是雁過留聲般的縹緲,可是我感覺到了,就像頭發感覺到微風那樣。我知道即使父親站在面前,我也認不出來,但是他會壹眼認出我。我迎著骨骼的他們走去,有時候是壹群,有時候是幾個,我自我展覽地站在他們前面,期望中間有壹個聲音響起:
“楊飛。”
我知道這個聲音會是陌生的,如同李青的聲音是陌生的那樣,但是我能夠從聲調裏分辨出父親的叫聲。在那個離去的世界裏,父親叫我的聲音裏總是帶著親切的聲調,在這個世界裏應該也是這樣。
這裏四處遊蕩著沒有墓地的身影,這些無法抵達安息之地的身影恍若移動的樹木,時而是壹棵壹棵分開的樹,時而是壹片壹片聚集起來的樹林。我行走在他們中間,仿佛行走在被砍伐過的森林裏。我期待父親的聲音出現,在前面、在後面、在左邊、在右邊,我的名字被他喊叫出來。
我不時遇到手臂上戴著黑紗的人,那些被黑紗套住的袖管顯得空空蕩蕩,我知道他們來到這裏很久了,他們的袖管裏已經沒有皮肉,只剩下骨骼。他們和我相視而笑,他們的笑容不是在臉上的表情裏,而是在空洞的眼睛裏,因為他們的臉上沒有表情了,只有石頭似的骨骼,但是我感受到那些會心的微笑,因為我們是同樣的人,在另外壹個世界裏沒有人會為我們戴上黑紗,我們都是在自己悼念自己。
壹個手臂上戴著黑紗的人註意到我尋找的眼神,他站立在我面前,我看著他骨骼的面容,他的前額上有壹個小小洞口,他發出友好的聲音。
“妳在找人?”他問我,“妳是找壹個人,還是找幾個人?”
“找壹個人。”我說,“我的父親,他可能就在這裏。”
“妳的父親?”
“他叫楊金彪。”
“名字在這裏沒有用。”
“他六十多歲……”
“這裏的人看不出年齡。”
我看著在遠處和近處走動的骨骼,確實看不出他們的年齡。我的眼睛只能區分高的和矮的,寬的和細的;我的耳朵只能區分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小的。
我想到父親最後虛弱不堪的模樣,我說:“他身高壹米七,很瘦的樣子……”
“這裏的人都是很瘦的樣子。”
我看著那些瘦到只剩下骨骼的人,不知道如何描述我的父親了。
他問我:“妳記得他是穿什麽衣服過來的?”
“鐵路制服,”我告訴他,“嶄新的鐵路制服。”
“他過來多久了?”
“壹年多了。”
“我見過穿其他制服的,沒見過穿鐵路制服的。”
“也許別人見過穿鐵路制服的。”
“我在這裏很久了,我沒見過,別人也不會見過。”
“也許他換了衣服。”
“不少人是換了衣服來到這裏的。”
“我覺得他就在這裏。”
“妳要是找不到他,他可能去墓地了。”
“他沒有墓地。”
“沒有墓地,他應該還在這裏。”
我在尋找父親的遊走裏不知不覺來到那兩個下棋的骨骼跟前,他們兩個盤腿坐在草地上,像是兩個雕像那樣專註。他們的身體紋絲不動,只是手在不停地做出下棋的動作。我沒有看見棋盤,也沒有看見棋子,只看見他們骨骼的手在下棋,我看不懂他們是在下象棋,還是在下圍棋。
壹只骨骼的手剛剛放下壹顆棋子,馬上又拿了起來,兩只骨骼的手立刻按住這只骨骼的手。兩只手的主人叫了起來:
“不能悔棋。”
壹只手的主人也叫了起來:“妳剛才也悔棋了。”
“我剛才悔棋是因為妳前面悔棋了。”
“我前面悔棋是因為妳再前面悔棋了。”
“我再前面悔棋是因為妳昨天悔棋了。”
“昨天是妳先悔棋,我再悔棋的。”
“前天先悔棋的是妳。”
“再前天是誰先悔棋?”
兩個人爭吵不休,他們互相指責對方悔棋,而且追根溯源,指責對方悔棋的時間從天數變成月數,又從月數變成年數。
兩只手的主人叫道:“這步棋不能讓妳悔,我馬上要贏了。”
壹只手的主人叫道:“我就要悔棋。”
“我不和妳下棋了。”
“我也不和妳下了。”
“我永遠不和妳下棋了。”
“我早就不想和妳下棋了。”
“我告訴妳,我要走了,我明天就去火化,就去我的墓地。”
“我早就想去火化,早就想去我的墓地了。”
我打斷他們的爭吵:“我知道妳們的故事。”
“這裏的人都知道我們的故事。”壹個說。
“新來的可能不知道。”另壹個糾正道。
“就是新來的不知道,我們的故事也爛大街了。”
“文明用語的話,我們的故事家喻戶曉。”
我說:“我還知道妳們的友情。”
“友情?”
他們兩個發出嘻嘻笑聲。
壹個問另壹個:“友情是什麽東西?”
另壹個回答:“不知道。”
他們兩個嘻嘻笑著擡起頭來,兩雙空洞的眼睛看著我,壹個問我:“妳是新來的?”
我還沒有回答,另壹個說了:“就是那個漂亮妞帶來的。”
兩個骨骼低下頭去,嬉笑著繼續下棋。好像剛才沒有爭吵,剛才誰也沒有悔棋。
他們下了壹會兒,壹個擡頭問我:“妳知道我們在下什麽棋?”
我看了看他們手上的動作說:“象棋。”
“錯啦,是圍棋。”
接著另壹個問我:“現在知道我們下什麽棋了吧?”
“當然,”我說,“是圍棋。”
“錯啦,我們下象棋了。”
然後他們兩個同時問我:“我們現在下什麽棋?”
“不是圍棋,就是象棋。”我說。
“又錯啦。”他們說,“我們下五子棋了。”
他們兩個哈哈大笑,兩個做出同樣的動作,都是壹只手捂住自己肚子的部位,另壹只手搭在對方肩膀的部位。兩個骨骼在那裏笑得不停地抖動,像是兩棵交叉在壹起的枯樹在風中抖動。
笑過之後,兩個骨骼繼續下棋,沒過壹會兒又因為悔棋爭吵起來。我覺得他們下棋就是為了爭吵,兩個妳來我往地指責對方悔棋的歷史。我站在那裏,聆聽他們快樂下棋的歷史和悔棋後快樂爭吵的歷史。他們其樂無窮地指責對方的悔棋劣跡,他們的指責追述到七年前的時候,我沒有耐心了,我知道還有七八年的時間等待他們的追述,我打斷他們。
“妳們誰是張剛?誰是李姓,”我遲疑壹下,覺得用當時報紙上的李姓男子不合適,我說,“誰是李先生?”
“李先生?”
他們兩個互相看看後又嘻嘻笑起來。
然後他們說:“妳自己猜。”
我仔細辨認他們,兩個骨骼似乎壹模壹樣,我說:“我猜不出來,妳們像是雙胞胎。”
“雙胞胎?”
他們兩個再次嘻嘻笑了。然後重新親密無間下起棋來,剛才暴風驟雨似的爭吵被我打斷後立刻煙消雲散。
接著他們故伎重演,問我:“妳知道我們在下什麽棋?”
“象棋,圍棋,五子棋。”我壹口氣全部說了出來。
“錯啦。”他們說,“我們在下跳棋。”
他們再次哈哈大笑,我再次看到他們兩個壹只手捂住自己肚子的部位,另壹只手搭在對方肩膀的部位,兩個骨骼節奏整齊地抖動著。
我也笑了。十多年前,他們兩個相隔半年來到這裏,他們之間的仇恨沒有越過生與死的邊境線,仇恨被阻擋在了那個離去的世界裏。
我尋找父親的行走周而復始,就像鐘表上的指針那樣走了壹圈又壹圈,壹直走不出鐘表。我也壹直找不到父親。
我幾次與壹個骨骼的人群相遇,有幾十個,他們不像其他的骨骼,有時聚集到壹起,有時又分散開去,他們始終圍成壹團行走著。如同水中的月亮,無論波浪如何拉扯,月亮始終圍成壹團蕩漾著。
我第四次與他們相遇時站住腳,他們也站住了,我與他們互相打量。他們的手連接在壹起,他們的身體依靠在壹起,他們組合在壹起像是壹棵茂盛的大樹,不同的樹枝高高低低。我知道他們中間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孩子,我向他們微笑,對他們說:
“妳們好!”
“妳好!”
我聽到他們齊聲回答,有男聲和女聲,有蒼老的聲音和稚嫩的聲音,我看到他們空洞的眼睛裏傳遞出來的笑意。
“妳們有多少人?”我問他們。
他們還是齊聲回答:“三十八個。”
“妳們為什麽總是在壹起?”我繼續問。
“我們是壹起過來的。”男聲回答。
“我們是壹家人。”女聲補充道。
他們中間響起壹個男孩的聲音:“為什麽妳只有壹個人?”
“我不是壹個人。”我低頭看看自己左臂上的黑紗說,“我在尋找我的父親,他穿著鐵路制服。”
我面前的骨骼人群裏有壹個聲音說話了:“我們沒有見過穿鐵路制服的人。”
“他可能是換了衣服來到這裏的。”我說。
壹個小女孩脆生生的聲音響起來:“爸爸,他是新來的嗎?”
所有的男聲說:“是的。”
小女孩繼續問:“媽媽,他是新來的嗎?”
所有的女聲說:“是的。”
我問小女孩:“他們都是妳的爸爸和媽媽?”
“是的。”小女孩說,“我以前只有壹個爸爸壹個媽媽,現在有很多爸爸很多媽媽。”
剛才的男孩問我:“妳是怎麽過來的?”
“好像是壹場火災。”我說。
男孩問身邊的骨骼們:“為什麽他沒有燒焦?”
我感受到了他們沈默的凝視,我解釋道:“我看見火的時候,聽到了爆炸,房屋好像倒塌了。”
“妳是被壓死的嗎?”小女孩問。
“可能是。”
“妳的臉動過了。”男孩說。
“是的。”
小女孩問我:“我們漂亮嗎?”
我尷尬地看著面前站立的三十八個骨骼,不知道如何回答小女孩脆生生的問題。
小女孩說:“這裏的人都說我們越來越漂亮了。”
“是這樣的,”男孩說,“他們說到這裏來的人都是越來越醜,只有我們越來越漂亮。”
我遲疑片刻,只能說:“我不知道。”
壹個老者的聲音在他們中間響了起來:“我們在火災裏燒焦了,來到這裏像是三十八根木炭,後來燒焦的壹片片掉落,露出現在的樣子,所以這裏的人會這麽說。”
這位老者向我講述起他們的經歷,另外三十七個無聲地聽著。我知道他們的來歷了,在我父親不辭而別的那壹天,距離我的小店鋪不到壹公裏的那家大型商場突然起火,銀灰色調的商場燒成了黑乎乎木炭的顏色。市政府說是七人死亡,二十壹人受傷,其中兩人傷勢嚴重。網上有人說死亡人數超過五十,還有人說超過壹百。我看著面前的三十八個骨骼,這些都是被刪除的死亡者,可是他們的親人呢?
我說:“妳們的親人為什麽也要隱瞞?”
“他們受到威脅,也拿到封口費。”老者說,“我們已經死了,只要活著的親人們能夠過上平安的生活,我們就滿足了。”
“孩子呢?他們的父母……”
“現在我們是孩子的父母。”老者打斷我的話。
然後他們手牽著手,身體靠著身體從我身旁無聲地走了過去。他們圍成壹團走去,狂風也不能吹散他們。
我遠遠看見兩個肉體完好的人從壹片枝繁葉茂的桑樹林那邊走了過來。這是衣著簡單的壹男壹女,他們身上所剩無幾的布料不像是穿著,像是遮蔽。他們走近時,我看清了女的身上只有黑色的內褲和胸罩,男的只有藍色的內褲。女的壹副驚魂未定的表情,蜷縮著身體走來,雙手放在大腿上,仿佛在遮蓋大腿。男的彎腰摟住她走來,那是保護的姿態。
他們走到我面前,仔細看著我,他們的目光像是在尋找記憶裏熟悉的面容。我看見失望的表情在他們兩個的臉上漸漸浮現,他們確定了不認識我。
男的問我:“妳是新來的?”
我點點頭,問他們:“妳們也是新來的,妳們是夫妻?”
他們兩個同時點頭,女的發出可憐的聲音:“妳在那邊見過我們的女兒嗎?”
我搖了搖頭,我說:“那邊人山人海,我不知道哪個是妳們的女兒。”
女的傷心地垂下了頭,男的用手撫摸她的肩膀,安慰她:“還會有新來的。”
女的重復我剛才的話:“可是那邊人山人海。”
男的繼續說:“總會有壹個新來的在那邊見過小敏。”
小敏?我覺得這是壹個曾經聽到過的名字。我問他們:“妳們是怎麽過來的?”
他們臉上掠過絲絲恐懼的神色,這是那個離去世界裏的經歷投射到這裏的陰影。他們的眼睛躲開我的目光,可能是眼淚在躲開我的目光。
然後男的講述起那個可怕的經歷。他們住在盛和路上,市裏要拆除那裏的三幢樓房,那裏的住戶們拒絕搬遷,與前來拆遷的對抗了三個多月,拆遷的在那個可怕的上午實施了強拆行動。他們夫妻兩個下了夜班清晨回家,叫醒女兒,給她做了早餐,女兒背著書包去上學,他們上床入睡。他們在睡夢裏聽到外面擴音器發出的壹聲聲警告,他們太疲倦了,沒有驚醒過來。此前他們聽到過擴音器發出的警告聲,見到過推土機嚴陣以待的架式,可是在與住戶們對峙之後,擴音器和推土機撤退而去。所以他們以為又是來嚇唬的,繼續沈溺在睡夢裏。直到樓房響聲隆隆劇烈搖晃起來,他們才被嚇醒。他們住在樓房的壹層,男的從床上跳起來,拉起女的朝門口跑去,男的已經打開屋門,女的突然轉身跑向沙發去拿衣服,男的跑回去拉女的,樓房轟然倒塌。
男的講述的聲音在這裏戛然而止,女的哭泣之聲響起了。
“對不起,對不起……”
“不要說對不起。”
“我不該拿衣服……”
“來不及了,妳就是不拿衣服也來不及了。”
“我不拿衣服,妳就不會跑回來,妳就能逃出去。”
“我逃出去了,妳怎麽辦?”
“妳逃出去了,小敏還有父親。”
我知道他們的女兒是誰了,就是那個穿著紅色羽絨服坐在鋼筋水泥的廢墟上,在寒風裏做作業等待父母回來的小女孩。
我告訴他們:“我見到過妳們的女兒,她叫鄭小敏。”
他們兩個同時叫了起來:“是的,是叫鄭小敏。”
我說:“她念小學四年級。”
“是的,”他們急切地問,“妳怎麽知道的?”
我對男的說:“我們通過電話,我是來做家教的那個。”
“妳是楊老師?”
“對,我是楊飛。”
男的對女的說:“他就是楊老師,我說我們收入不多,他馬上答應每小時只收三十元。”
女的說:“謝謝妳。”
在這裏聽到感謝之聲,我苦笑了。
男的問我:“妳怎麽也過來了?”
我說:“我坐在壹家餐館裏,廚房起火後爆炸了。我和妳們同壹天過來的,比妳們晚幾個小時。我在餐館裏給妳手機打過電話,妳沒有接聽。”
“我沒有聽到手機響。”
“妳那時候在廢墟下面。”
“是的,”男的看著女的說,“手機可能被壓壞了。”
女的急切地問:“小敏怎麽樣了?”
“我們約好下午四點到妳們家,我到的時候那三幢樓房沒有了……”
我猶豫之後,沒有說他們兩個在盛和路強拆事件中的死亡被掩蓋了。我想,壹個他們夫妻兩人同時因公殉職的故事已經被編造出來,他們的女兒會得到兩個裝著別人骨灰的骨灰盒,然後在壹個美麗的謊言裏成長起來。
“小敏怎麽樣了?”女的再次問。
“她很好,”我說,“她是我見過的最懂事的孩子,妳們可以放心,她會照顧好自己的。”
“她只有十壹歲。”女的心酸地說,“她每次出門上學,走過去後都會站住腳,喊叫爸爸和媽媽,等我們答應了,她說壹聲‘我走了’,再等我們答應了,她才會去學校。”
“她和妳說了什麽?”男的問。
我想起了在寒風裏問她冷不冷,她說很冷,我讓她去不遠處的肯德基做作業,我說那裏暖和,她搖搖頭,說爸爸媽媽回來會找不到她的。她不知道父母就在下面的廢墟裏。
我再次猶豫後,還是把這些告訴了他們,最後說:“她就坐在妳們上面。”
我看見淚水在他們兩個的臉上無聲地流淌,我知道這是不會枯竭的淚水。我的眼睛也濕潤了,趕緊轉身離去,走出壹段路程後,身後的哭聲像潮水那樣追趕過來,他們兩個人哭出了人群的哭聲。我仿佛看見潮水把身穿紅色羽絨服的小女孩沖上沙灘,潮水退去之後,她獨自擱淺在那邊的人世間。
我看到了這裏的盛宴。在壹片芳草地上,有碩果累累的果樹,有欣欣向榮的蔬菜,還有潺潺流動的河水。死者分別圍坐在草地上,仿佛圍坐在壹桌壹桌的酒席旁,他們的動作千姿百態,有埋頭快吃的,有慢慢品嘗的,有說話聊天的,有抽煙喝酒的,有舉手幹杯的,有吃飽後摸起了肚子的……我看見幾個肉體的人和幾個骨骼的人穿梭其間,他們做出來的是端盤子的動作和斟酒的動作,我知道這幾個是服務員。
我走了過去,壹個骨骼的人迎上來說:“歡迎光臨譚家菜。”
這個少女般的聲音說出來的譚家菜讓我壹怔,然後我聽到壹個陌生的聲音喊叫我的名字。
“楊飛。”
我沿著聲音望去,看到譚家鑫壹瘸壹拐地快步走了過來,他的右手是托著壹個盤子的動作。我看見了他臉上的喜悅表情,這是在那個離去的世界裏沒有見過的表情,在那裏他面對我的時候只有苦笑。他走到我跟前,欣喜地說:
“楊飛,妳是哪天到這裏的?”
“昨天。”我說。
“我們過來四天了。”
譚家鑫說話時,右手壹直是托著盤子的動作。他回頭喊叫他的妻子和女兒,還有女婿。他大聲喊叫他們的名字,把自己的喜悅傳遞給他們:
“楊飛來啦。”
我見到譚家鑫的妻子、女兒和女婿走來了,他們的手都是端著盤子和提著酒瓶的動作。譚家鑫對著走來的他們說:
“譚家菜今天開張,楊飛今天就來了。”
他們走到我跟前,笑呵呵地上下打量我。譚家鑫的妻子說:“妳看上去瘦了壹些。”
“我們也瘦了。”譚家鑫快樂地說,“來到這裏的人都會越來越瘦,這裏的人個個都是好身材。”
譚家鑫的女兒問我:“妳怎麽也到這裏來了?”
“我沒有墓地。”我說,“妳們呢?”
譚家鑫的臉上掠過壹絲哀愁,他說:“我們的親戚都在廣東,他們可能還不知道我們的事。”
譚家鑫的妻子說:“我們壹家人在壹起。”
快樂的表情回到了譚家鑫的臉上,他說:“對,我們壹家人在壹起。”
我問譚家鑫:“妳的腿斷了?”
譚家鑫笑聲朗朗地說:“腿斷了我走路更快。”
這時那邊響起了叫聲:“我們的菜呢,我們的酒呢……”
譚家鑫轉身對那邊喊叫壹聲:“來啦。”
譚家鑫右手是托著盤子的動作,壹瘸壹拐地快步走去。他的妻子、女兒和女婿是端著盤子提著酒瓶的動作,他們向著那邊急匆匆地走去。
譚家鑫走去時回頭問我:“吃什麽?”
“還是那碗面條。”
“好咧。”
我尋找到壹個座位,坐在草地上,感覺像是坐在椅子上。我的對面坐著壹個骨骼,他做出來的只有飲酒的動作,沒有用筷子夾菜吃飯的動作,他空洞的眼睛望著我手臂上的黑紗。
我覺得他的穿著奇怪,黑色的衣服看上去很寬大,可是沒有袖管,暴露出了骨骼的手臂和肩膀,黝黑的顏色仿佛經歷長年累月的風吹日曬。黑衣在兩側肩膀處留下了毛邊,兩只袖管好像是被撕下的。
我們互相看著,他先說話了:“哪天過來的?”
“第五天了,”我說,“到這裏是昨天。”
他舉起酒杯壹飲而盡,放下酒杯後是斟酒的動作。
他感嘆道:“孤零零壹個人。”
我低頭看看自己手臂上的黑紗。
“妳還知道給自己戴上黑紗過來,”他說,“有些孤零零的冒失鬼來到這裏,沒戴黑紗,看見別人戴著黑紗,就羨慕上了,就來纏著我,要我撕給他們壹截袖管當作黑紗。”
我看著他暴露在外的骨骼的手臂和肩膀,微微笑了起來。他做出了舉杯壹飲而盡和放下酒杯的動作。
他用手比劃著說:“原來的袖管很長,都超過手指,現在妳看看,兩個肩膀都露出來了。”
“妳呢,”我問他,“妳不需要黑紗?”
“我在那邊還有家人,”他說,“他們可能忘掉我了。”
他做出拿起酒瓶的動作和給酒杯斟酒的動作,動作顯示是最後壹杯了,他再次做出壹飲而盡的動作。
“好酒。”他說。
“妳喝的是什麽酒?”我問他。
“黃酒。”他說。
“什麽牌子的黃酒?”
“不知道。”
我笑了,問他:“妳過來多久了?”
“忘了。”
“忘了的話,應該很久了。”
“太久了。”
“妳在這裏應該見多識廣,我請教壹個問題。”我說出了思緒裏突然出現的念頭,“我怎麽覺得死後反而是永生。”
他空洞的眼睛看著我沒有說話。
我說:“為什麽死後要去安息之地?”
他似乎笑了,他說:“不知道。”
我說:“我不明白為什麽要把自己燒成壹小盒灰?”
他說:“這個是規矩。”
我問他:“有墓地的得到安息,沒墓地的得到永生,妳說哪個更好?”
他回答:“不知道。”
然後他扭頭喊叫:“服務員,埋單。”
壹個骨骼的女服務員走過來說:“五十元。”
他做出了將五十元放在桌子上的動作,對我點點頭後起身,離去時對我說:
“小子,別想那麽多。”
我看著他身上寬大的黑色衣服和兩條纖細的骨骼手臂,不由想到甲殼蟲。他的背影逐漸遠去,消失在其他骨骼之中。
譚家鑫的女婿走過來,雙手是端著壹碗面條的動作,隨後是遞給我的動作,我的雙手是接過來的動作。
我做出把那碗面條放在草地上的動作,感覺像是放在桌子上。然後我的左手是端著碗的動作,右手是拿著筷子的動作,我完成了吃壹口面條的動作,我的嘴裏開始了品嘗的動作。我覺得和那個已經離去世界裏的味道壹樣。
我意識到四周充滿歡聲笑語,他們都在快樂地吃著喝著,同時快樂地數落起了那個離去世界裏的毒大米、毒奶粉、毒饅頭、假雞蛋、皮革奶、石膏面條、化學火鍋、大便臭豆腐、蘇丹紅、地溝油。
在朗朗笑聲裏,他們贊美起了這裏的飲食,我聽到新鮮美味健康這樣的詞匯接踵而來。
壹個聲音說:“全中國只有兩個地方的食品是安全的。”
“哪兩個地方?”
“這裏是壹個。”
“還有壹個呢?”
“還有壹個就是那邊的國宴。”
“說得好,”有人說,“我們在這裏享受的是國宴的吃喝待遇。”
我微笑時發現自己吃面條的動作沒有了,我意識到已經吃完,這時聽到旁邊有人喊叫:
“埋單。”
壹個骨骼的服務員走過來,對他說:“八十七元。”
他對服務員說:“給妳壹百。”
服務員說:“找妳十三元。”
他說:“謝啦。”
整個結賬過程只是對話,動作也沒有。這時譚家鑫壹瘸壹拐向我走過來,他手裏是端著壹個盤子的動作,我知道是送給我壹個果盤,我做出接過來的動作。他在我對面坐下來,對我說:
“這是剛剛摘下來的新鮮水果。”
我開始了吃水果的動作,我感覺到了甘美香甜,我說:“譚家菜這麽快又開張了。”
“這裏沒有公安、消防、衛生、工商、稅務這些部門。”他說,“在那邊開壹家餐館,消防會拖上妳壹兩年,說妳的餐館有火災隱患;衛生會拖上妳壹兩年,說妳衛生條件不合格。妳只有給他們送錢送禮了,他們才允許妳開業。”
隨即他有些不安地問我:“妳沒有恨我們吧?”
“為什麽要恨妳們?”
“我們把妳堵在屋子裏。”
我想起在那個世界裏的最後情景,譚家鑫的眼睛在煙霧裏瞪著我,對我大聲喊叫。
我說:“妳好像在對我喊叫。”
“我叫妳快跑。”他嘆了壹口氣說,“我們誰也沒有堵住,就堵住了妳。”
我搖搖頭說:“不是妳們堵住我,是我自己沒有走。”
我沒有告訴他那張報紙和報紙上關於李青自殺的報道,這個說起來過於漫長。
也許以後的某壹個時刻,我會向他娓娓道來。
譚家鑫仍然在內疚裏不能自拔,他向我解釋為何在廚房起火後,他們要堵住大門讓顧客付錢後再走,他說他的飯館經營上入不敷出三年多了。
“我昏了頭。”他說,“害了自己,害了家人,也害了妳。”
“來到這裏也不錯,”我說,“我父親也在這裏。”
“妳父親在這裏?”譚家鑫叫了起來,“他怎麽沒有壹起來?”
“我還沒有找到他。”我說,“我覺得他就在這裏。”
“妳找到後,壹定要帶他過來。”譚家鑫說。
“我會帶他過來的。”我說。
譚家鑫在我對面坐了壹會兒,他不再是愁眉不展,而是笑容滿面。他起身離開時再次說,找到父親後壹定要帶他到這裏來嘗壹嘗。
然後我結賬了,壹個骨骼的女聲走過來,我想她是譚家鑫剛剛招收來的服務員。她對我說:
“面條十壹元,果盤是贈送的。”
我說:“給妳二十元。”
她說:“找妳九元。”
我們之間也是只有對話,沒有動作。當我起身走去時,這個骨骼的女聲在後面熱情地說:
“謝謝光臨!歡迎下次再來!”
在壹片青翠欲滴的竹林前,壹個袖管上戴著黑紗的骨骼走到我面前。我註意到他前額上的小小圓洞,我見過他,向他打聽過父親的行蹤。我向他微笑,他也在微笑,他的微笑不是波動的表情,而像輕風壹樣從他空洞的眼睛和空洞的嘴裏吹拂出來。
“那裏有篝火。”他說,“就在那裏。”
我順著他的手指望向天邊似的望向遠處。遠處的草地正在寬廣地鋪展過去,草地結束的地方有閃閃發亮的跡象,像是壹根絲帶,我感到那是河流。那裏還有綠色的火,看上去像是打火機打出來的微小之火。我看見壹些骨骼的人從山坡走下去,從樹林走出來,陸續走向那裏。
“過去坐壹會兒吧。”他說。
“那是什麽地方?”我問他。
“河邊,”他說,“有壹堆篝火。”
“妳們經常去那裏?”
“不是經常,每隔壹段時間去壹次。”
“這裏的人都去?”
“不是,”他看看我袖管上的黑紗,又指指自己袖管上的黑紗說,“是我們這樣的人。”
我明白了,那裏是自我悼念者的聚集之地。我點點頭,跟隨他走向絲帶般的河流和微小的篝火。我們的腳步在草叢裏延伸過去,青草發出了噝噝響聲。
我看著他袖管上的黑紗,問他:“妳是怎麽過來的?”
“快九年了。”他說。
他的聲音裏出現了追憶的調子:“那時候我結婚兩年多,我老婆有精神病,結婚前我不知道,只和她見過三次,覺得她笑起來有些奇怪,我心裏不踏實,我父母覺得沒什麽,女方的家境很好,嫁妝很多,嫁妝裏還有壹張兩萬元的存折。我們那邊的農村很窮,找對象結婚都是父母做主,兩萬元可以蓋壹幢兩層的樓房,我父母就定下這門親事,結婚後知道她有精神病。
“她還好,不打不鬧,就是壹天到晚嘿嘿笑個不停,什麽活兒都不幹。我父母後悔了,覺得對不起我,但是他們不讓我離婚,說樓房蓋起來了,用的是她嫁妝的錢,不能過河拆橋。我也沒想到要離婚,我想就這樣過下去吧,再說她在精神病裏面算是文靜的,晚上睡著了和正常人沒什麽兩樣。
“那年的夏天,她離家出走,她自己也不知道走到什麽地方。我出去找她,我父母和哥哥嫂子也出去找她,去了很多地方,到處打聽她,沒有她的消息。我們找了三天,找不到她,就去告訴她娘家的人,她娘家的人懷疑是我把她害死的,就去縣裏公安局報案。
“她出走的第五天,離我們村兩公裏遠的地方有壹個池塘裏浮起來壹具女屍,夏天太熱,女屍被發現時已經腐爛,認不出樣子,警察讓我和她娘家的人去辨認,我們都認不出來,只是覺得女屍的身高和她差不多。警察說女屍淹死和她出走是同壹天,我覺得就是她,她娘家的人也覺得就是她。我想她可能是不小心走進池塘裏去的,她有精神病,不知道走進池塘會淹死的。我心裏還是有點難過,不管怎樣我們做了兩年多的夫妻。
“過了兩天,警察來問我,她出走那天我在做什麽,那天我進城了,我是晚上回家發現她不在的。警察問有沒有人可以證明我進城了,我想了想說沒有,警察給我做了筆錄就走了。她娘家的人認定是我殺了她,警察也這麽認為,就把我抓了起來。
“我父母和哥哥嫂子開始不相信我會殺她,後來我自己承認殺了她,他們就相信了。他們很傷心,也怨恨我,我讓他們做人都擡不起頭來,我們那邊的農村就是這樣,家裏出了個殺人犯,全家人都不敢見人。法庭宣判我死刑時他們壹個都沒有來,她娘家的人都來了。我不怪他們,我被抓起來後,他們想來見我,警察不讓他們見,他們都是老實巴交的人,不知道我是冤枉的。
“我承認殺了她是沒有辦法,警察把我吊起來打,逼我認罪,屎尿都被他們打出來了,我的兩只手被捆綁起來吊了兩天,因為失血有四根手指黑了,他們說是壞死了。以後他們就把我反吊起來打,兩只腳吊在上面,頭朝下,反吊起來打最疼的不是身上了,是眼睛,汗水是鹹的,流進眼睛跟針在紮著眼睛那麽疼。我想想還是死了好,就承認了。”
他停頓了壹下問我:“為什麽眉毛要長在眼睛上面?”
“為什麽?”
“為了擋汗水。”
我聽到他的輕輕笑聲,像是獨自的微笑。
他指指自己的後腦,又指指自己前額上的圓洞說:“子彈從後面打進去,從這裏出來的。”
他低頭看看自己袖管上的黑紗,繼續說:“我來到這裏,看見有人給自己戴著黑紗,也想給自己戴,我覺得那邊沒有人給我戴黑紗,我的父母和哥哥嫂子不敢戴,因為我是殺人犯。我看見壹個人,穿著很長很寬的黑衣服,袖管很長,我問他能不能撕下壹截袖管給我,他知道我要它幹什麽,就撕下來壹截送給我。我戴上黑紗後心裏踏實了。
“在我後面過來的人裏邊,有壹個知道我的事,他告訴我,我被槍斃半年後,我的精神病老婆突然回家了,她衣服又臟又破,臉上也臟得沒人能認出來,她站在家門口嘿嘿笑個不停,站了半天,村裏有人認出了她。
“那邊的人終於知道我是冤枉的,我父母和哥哥嫂子哭了兩天,覺得我太可憐了,政府賠償給他們五十多萬,他們給我買了壹塊很好的墓地……”
“妳有墓地?”我問他,“為什麽還在這裏?”
“我那時候把黑紗取下來,扔在壹棵樹下,準備去了,走出了十多步,舍不得,又回去撿起來戴上。”他說,“戴上黑紗,我就不去了。”
“妳不想去安息了?”我問。
“我想去,”他說,“我那時候想反正有墓地了,不用急,什麽時候想去了就去。”
“多少年了?”
“八年了。”
“墓地還在嗎?”
“還在,壹直在。”
“妳打算什麽時候去?”
“以後去。”
我們走到了自我悼念者的聚集之地。我的眼前出現寬闊的河流,閃閃發亮的景象也寬闊起來。壹堆綠色篝火在河邊熊熊燃燒,跳躍不止的綠色火星仿佛是飛舞的螢火蟲。
已經有不少戴著黑紗的骨骼坐在篝火旁,我跟著他走了進去,尋找可以坐下的位置,我看到壹些坐下的骨骼正在移動,為我們騰出壹個又壹個空間,我站在那裏猶豫不決,不知道應該走向哪個。看到他走到近旁的位置坐下,我也走過去坐下來。我擡起頭來,看見還有正在走來的,有的沿著草坡走來,有的沿著河邊走來,他們像涓涓細流那樣匯集過來。
我聽到身旁的骨骼發出友好的聲音:“妳好。”
“妳好”形成輕微的聲浪,從我這裏出發,圍繞著篝火轉了壹圈,回到我這裏後掉落下去。
我悄聲問他:“他們是在問候我嗎?”
“是的,”他說,“妳是新來的。”
我感到自己像是壹棵回到森林的樹,壹滴回到河流的水,壹粒回到泥土的塵埃。
戴著黑紗的陸續坐了下來,仿佛是聲音陸續降落到安靜裏。我們圍坐在篝火旁,寬廣的沈默裏暗暗湧動千言萬語,那是很多的卑微人生在自我訴說。每壹個在那個離去的世界裏都有著不願回首的辛酸事,每壹個都是那裏的孤苦伶仃者。我們自己悼念自己聚集到壹起,可是當我們圍坐在綠色的篝火四周之時,我們不再孤苦伶仃。
沒有說話,沒有動作,只有無聲的相視而笑。我們坐在靜默裏,不是為了別的什麽,只是為了感受我們不是壹個,而是壹群。
我在靜默的圍坐裏聽到火的聲音,是舞動聲;聽到水的聲音,是敲擊聲;聽到草的聲音,是搖曳聲;聽到樹的聲音,是呼喚聲;聽到風的聲音,是沙沙聲;聽到雲的聲音,是漂浮聲。
這些聲音仿佛是在向我們傾訴,它們也是命運多舛,它們也是不願回首。然後,我聽到夜鶯般的歌聲飛來了,飛過來壹段,停頓壹下,又飛過來壹段……
我聽到壹個耳語般的聲音:“妳來了。”
我走向這個陌生的聲音,像是雨水從屋檐滴到窗臺上的聲音,清晰和輕微。我判斷出這是壹個女人的聲音,飽經風霜之後,聲音裏有著黃昏時刻的暗淡,可是仍然節奏分明,像是有人在敲門,壹下,兩下,三下。
“妳來了。”
我有些疑惑,這個聲音是不是在對我說?可是聲音裏有著遙遠的親切,記憶深處的那種親切,讓我覺得聲音就是在對我說,說了壹遍又壹遍。接著我又聽到了夜鶯般的歌聲,波浪壹樣蕩漾過來。“妳來了”的聲音踏著夜鶯般的歌聲向我而來。
我走向夜鶯般的歌聲和“妳來了”的聲音。
我走進壹片樹林,感到夜鶯般的歌聲是從前面的樹上滑翔下來的。我走過去,註意到樹葉越來越寬大,然後我看見壹片片寬大搖曳的樹葉上躺著只剩下骨骼的嬰兒,他們在樹葉的搖籃裏晃晃悠悠,唱著動人魂魄的歌聲。我伸出手指,壹個個數過去,數到二十七個以後沒有了,我放下手。這個數字讓我心裏為之壹動,我的記憶瞬間追趕上那個離去的世界,我想起漂浮在河水裏和丟棄在河岸邊的二十七個被稱為醫療垃圾的死嬰。
“妳來了。”
我看見壹個身穿寬大白色衣服的骨骼坐在樹木之間芳草叢中,她慢慢站了起來,嘆息壹聲,對我說:
“兒子,妳怎麽這麽快就來了?”
我知道她是誰了,輕輕叫了壹聲:“媽媽。”
李月珍走到我跟前,空洞的眼睛凝視我,她的聲音飄忽不定,她說:“妳看上去有五十多歲了,可是妳只有四十壹歲。”
“妳還記得我的年齡。”我說。
“妳和郝霞同齡。”她說。
此刻郝霞和郝強生在另壹個世界裏的美國,我和李月珍在這個世界裏的這裏。郝霞和郝強生離開時,我送他們到機場,他們飛到上海後再轉機去美國。我請求郝強生,讓我來捧著骨灰盒,我要送這位心裏的母親最後壹程。
“我看見妳們去了機場,看見妳捧著骨灰盒。”李月珍說著搖了搖頭,“不是我的骨灰,是別人的。”
我想到別人的骨灰以她的名義安葬在了美國,我告訴她:“郝霞說已經給妳找好安息之地,說以後爸爸也在那裏。”
我沒有說下去,因為我想到多年後郝強生入土時,不會和李月珍共同安息,他將和壹個或者幾個殘缺不全的陌生者共處壹隅。
李月珍空洞的眼睛裏滴出了淚珠,她也想到這個。淚珠沿著她石頭似的臉頰流淌下去,滴落在幾根青草上。然後她空洞的眼睛裏出現笑意,她擡頭看看四周夜鶯壹樣歌唱的嬰兒,她說:
“我在這裏有二十七個孩子,現在妳來了,我就有二十八個了。”
她只剩下骨骼的手指撫摸起了我左臂上的黑布,她知道我是在悼念自己,她說:
“可憐的兒子。”
我冰冷的心裏出現了火焰跳躍般的灼熱。有壹個嬰兒不小心從樹葉上滾落下來,他吱吱哭泣著爬到李月珍跟前,李月珍把他抱到懷裏輕輕搖晃了壹會兒,再把他放回到寬大的樹葉上,這個嬰兒立刻快樂地加入到其他嬰兒夜鶯般的歌唱裏去了。
“妳是怎麽過來的?”李月珍問我。
我把自己在那邊的最後情景告訴了她,還說了李青千裏迢迢來向我告別。
她聽後嘆息壹聲說:“李青不應該離開妳。”
也許是吧,我心想。如果李青當初沒有離開我,我們應該還在那個世界裏過著平靜的生活,我們的孩子應該上小學了,可能是壹個中學生。
我想起李月珍和二十七個死嬰的神秘失蹤,殯儀館聲稱已經將她和二十七個死嬰火化了,網上有人說她和二十七個死嬰的骨灰是從別人的骨灰盒裏分配出來的。
“我知道這些,”她說,“後面過來的人告訴我的。”
我擡頭看看躺在寬大樹葉上發出夜鶯般歌聲的嬰兒們,我說:“妳把他們抱到這裏?”
“我沒有抱他們,”她說,“我走在前面,他們在後面爬著。”
李月珍說那天深夜沒有聽到轟然響起的塌陷聲,但是她醒來了。此前她沈溺在三個沈睡裏,她在第壹個沈睡裏見到遼闊的混沌,天和地渾然壹體,壹道光芒像地平線那樣出現,然後光芒潮水似的湧來,天和地分開了,早晨和晚上也分開了;在第二個沈睡裏見到空氣來了,快速飛翔和穿梭;在第三個沈睡裏見到水從地上蔓延開來,越來越像大海。
然後她醒來了,身體似乎正從懸崖掉落,下墜的速度讓她的身體豎立起來,她慢慢扯開那塊白布,像是清除堵在門前的白雪,她的雙腳開始走動,走出天坑底下的太平間,冷清的月光灑滿天坑,她的雙腳踩到犬牙交錯似的坑壁,以躺著的姿態走出天坑。
她走在被燈光照亮的城市裏,行人車輛熙熙攘攘,景物依舊,可是她的行走置身其外。
她像是回家那樣自然而然走到自己居住的樓房前,可是她不能像回家那樣走進去,無論她的雙腿如何擺動,也無法接近那幢樓房,那是她離開人世的第三個夜晚。她看見六樓的窗口閃過壹個女人的身影,心裏怦然而動,那是郝霞,女兒回來了。
接下去的兩個晝夜裏,她沒有停止自己向前的步伐,可是漸行漸遠。那個窗口壹直沒有出現郝強生,也沒有出現我,郝霞也只是出現壹次。她看見陸續有人搬著桌子椅子櫃子,搬著茶幾沙發,搬著床從樓房裏出來,她知道這些與她朝夕相處幾十年的家具賣掉了,那套房子也賣掉了,她的丈夫和女兒即將飛往美國。
她終於看見我們,在下午的時刻,郝強生捧著骨灰盒在郝霞的攙扶下走出樓房,郝霞右手還提著壹只很大的行李袋,我提著兩個很大的行李箱跟在後面,我們三個站在路邊,壹輛出租車停下,我和司機壹起把兩個行李箱和郝霞手裏的行李袋放進後備箱。她看見我對郝強生說了幾句話,郝強生把骨灰盒交給我,我捧起骨灰盒,郝霞與郝強生坐進後座,我坐進前座,出租車駛去了。
她知道這是永別的時刻,郝強生和郝霞要去遙遠的美國,她潸然淚下,身體奔跑起來,可是奔跑仍然讓她遠離我們,她站住了,看著出租車消失在街上的車流裏。
她哭出了聲音,哭了很久後聽到身後有噝噝的聲響,仿佛也是哭泣之聲,她回頭看見二十七個嬰兒排成壹隊匍匐在地,他們似乎和她壹樣傷心。當她的哭泣停止後,他們噝噝的哭聲也停止了。她不知道他們跟在她的後面爬出天坑,又壹直跟著她爬到這裏。她看著前面漸漸遠去的城市,又回頭看看二十七個嬰兒,知道自己失去了什麽,又得到了什麽。
她輕聲對嬰兒們說:“走吧。”
身穿白色衣褲的李月珍緩步前行,二十七個嬰兒排成壹隊在她後面爬行。陽光是陳舊的黃色,他們穿過鬧哄哄的城市,走進寧靜之中,迎來銀灰色的月光,他們在寧靜裏越走越深。
越過生與死的邊境線之後,李月珍踏上壹片芳草地,青青芳草摩擦了後面爬行的二十七個嬰兒的脖子,癢癢的感覺讓二十七個嬰兒發出咯吱的笑聲。芳草地結束之後是壹條閃閃發亮的河流,李月珍走入河水,河水慢慢上升到她的胸口,又慢慢下降到她的腳下,她來到對岸;二十七個嬰兒在水面上爬行過去,他們嗆到水了,咳嗽的聲音壹直響到對岸。他們過河入林,在樹林裏李月珍不知不覺哼唱起某壹個曲調,後面二十七個嬰兒也哼唱起來。李月珍停止哼唱後,二十七個嬰兒沒有停止,夜鶯般的歌聲壹直響到現在。
“妳父親來過,”李月珍說,“楊金彪來過。”
我吃驚地看著她,她繼續說:“他走了很遠的路來到這裏,他很累,在這裏躺了幾天,壹直在念叨妳。”
“他不辭而別去了哪裏?”
“他上了火車,去了當年丟棄過妳的地方。”
我銘記著與父親最後壹夜的對話。我們擠在小店鋪的狹窄床上,窗外路燈的光亮似乎昏昏欲睡,夜風正在撫摸我們的窗戶。父親第壹次在我面前哭了,他講述我四歲時,為了壹個姑娘把我丟棄在那個陌生城市的壹塊石頭上,他描述那塊青色石頭的粗糲和石頭表面的平滑,他把我放在平滑的上面。他為此指責自己的狠心,壹聲又壹聲。可是父親不辭而別,我沒有想到這個,我去了很多地方找他,卻沒有想到他會坐上火車去了那裏。
我父親穿上嶄新的鐵路制服,這是他最新的制服,壹直舍不得穿,直到離去的時候才穿在身上。他拖著虛弱不堪的身體登上火車,吃力地找到自己的座位,身體剛剛在座位上安頓下來,火車就啟動了。看著站臺緩緩後退而去,他突然感到自己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他不知道這麽壹走是否還能再見到我。
父親告訴李月珍,在那個晚上,他沒有睡著,壹直在聽著我均勻的呼吸聲和時而出現的鼾聲,中間有壹會兒我沒有聲息,他擔心了,伸手摸了我的臉和脖子,我被驚醒,支起身體看著他,他閉上眼睛假裝睡著。他說我在黑暗裏摸了摸他的身體,小心翼翼地把他的胳膊放進被子裏。
我搖搖頭,告訴李月珍:“我不知道這些。”
李月珍指了指身前樹下的草叢說:“他就躺在這裏,壹直在說話。”
我父親找到了那個地方,可是沒有找到那塊青色的石頭和那片樹林,還有那座石板橋和那條沒有河水的小河;他記得石板橋的對面應該有壹幢房屋,房屋裏應該有孩子們唱歌的聲音,他沒有找到那幢房子,沒有聽到孩子們的歌聲。父親告訴李月珍,壹切都變了,連火車也變了。當年他和我乘坐的火車黎明時刻駛出站臺,中午才到達那座小城。後來他獨自壹人乘坐的仍然是黎明時刻出發的火車,可是壹個多小時就到了那裏。
李月珍問他:“妳還記得那個地名?”
“記得,”他說,“河畔街。”
他在早晨的陽光裏走出那個城市的車站,他的身旁都是背著行李袋拖著行李箱快步走去的旅客,他們像沖鋒壹樣。他緩慢移動的身體上空空蕩蕩,沒有行李袋也沒有行李箱,可是他的身體比那些行李袋和行李箱都要沈重。他緩步走向出站口,他的雙手無力下垂,幾乎沒有甩動。
他站在車站前的廣場上,聲音虛弱地詢問從身旁匆忙經過的那些健康身體是不是本地人,他詢問了二十多個,只有四個說自己是本地人,他向他們打聽怎麽去河畔街,前面三個年輕人都不知道河畔街在哪裏,第四個是老人,知道河畔街,告訴他需要換乘三次公交車才能到那裏。他登上壹輛公交車,拖著奄奄壹息的身體,在舉目無親的城市裏尋找起那個遺棄過我的陌生之地。
李月珍問他:“為什麽去那裏?”
他說:“我就想在那塊石頭上坐壹會兒。”
他找到那個地方的時候已是下午。擁擠的公交車讓他筋疲力盡,下了壹輛之後他需要在街邊坐上很長時間,才有力氣登上另壹輛。他輾轉三次公交車,在距離河畔街三百多米的公交車站下車。接下來的三百米路程對於他比三千米還要漫長,他艱難前行,步履沈重,兩只腳仿佛是兩塊石頭壹樣提不起來,只能在人行道上慢慢移動,走上五六米之後,他就要扶住壹棵樹休息片刻。他看到街邊有壹家小吃店,覺得自己應該吃點東西,就在店外人行道上擺著的凳子上坐下來,雙臂擱在桌子上支撐身體,他給自己要了壹碗餛飩。他吃下去三口就嘔吐起來,吐在隨身攜帶的塑料袋裏。坐在旁邊吃著的人壹個個端起飯碗跑進小吃店裏面,他聲音微弱地對他們說了幾聲對不起,接著繼續吃,繼續嘔吐。然後他吃完了,也吐完了,他覺得吃下去的比吐出來的多,身體有壹些力氣了,他搖晃著站起來,搖晃著走向河畔街。
他告訴李月珍:“那地方全是高樓,住了很多人。”
昔日的小河沒有了,昔日的石板橋也沒有了。他聽到孩子們的聲音,不是昔日孩子們歌唱的聲音,而是今日孩子們嬉戲的聲音。他們在壹個兒童遊玩的區域裏坐著滑梯大聲喊叫,孩子們的爺爺奶奶壹邊聊天壹邊看護他們。這裏已是壹個住宅小區,高樓下的小路像是壹條條夾縫,車和人在裏面往來。他打聽小河在哪裏,石板橋在哪裏,住在這裏的人都是從別處搬過來的,他們說沒有小河沒有石板橋,從來都沒有。他問這裏是叫河畔街嗎?他們說是。他又問這裏以前叫河畔街嗎?他們說以前好像也叫河畔街。
“沒有小河了,還叫河畔街?”李月珍問他。
“地名沒有變,其他都變了。”他說。
他用虛弱的聲音繼續向他們打聽這裏有沒有小樹林,樹林的草叢裏還應該有壹塊青色的石頭。有壹個人告訴他,沒有小樹林,草叢倒是有,在小區旁邊的公園裏,草叢裏也有石頭。他問公園有多遠,那人說很近,只有兩百米,可是這兩百米對他來說仍然是壹次艱難的跋涉。
他走到那個公園時已是黃昏,落日的余輝照耀著壹片草地,草地上錯落有致凸顯的幾塊石頭上有著夕陽溫暖的顏色,他在這幾塊石頭裏尋找記憶中的那塊石頭,感到中間那塊有些發青的石頭很像我當初坐在上面的那壹塊。他緩慢地走到那塊石頭旁,想坐在上面,可是身體不聽使喚滑了下去。他只能靠著石頭坐在草地上,那壹刻他感到自己沒有力氣再站起來了。他的頭歪斜在石頭上,無力地看著近處壹個身穿藍色破舊衣服的流浪漢在壹個垃圾桶裏找吃的,流浪漢從桶裏找出壹個可樂瓶,擰開蓋子往自己嘴裏倒進剩下的幾滴可樂。流浪漢舉起的手在張開的嘴巴上搖動幾下,又把可樂瓶扔回垃圾桶,然後轉過身來盯著他。流浪漢的眼睛像鷹眼壹樣看著他,他垂下了眼睛。過了壹會兒,他擡起眼睛看到流浪漢坐在垃圾桶旁的壹把椅子上,流浪漢的目光仍然盯著他,他感覺那目光盯住自己身上嶄新的鐵路制服。
“我看見楊飛了,”他對李月珍說,“就在那塊石頭上。”
這是彌留之際,他沈沒在黑暗裏,像是沈沒在井水裏,四周寂靜無聲。高樓上的燈光熄滅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也熄滅了。隨即突然出現壹片燦爛光芒,當初他丟棄我的情景在光芒裏再現了。他看見四歲的我坐在石頭上,穿著壹身藍白相間的小水手服,這是他決定丟棄我時給我買來的。壹個小水手坐在青色的石頭上,快樂地搖晃著兩條小腿。他悲哀地對我說,我去買點吃的;我快樂地說,爸爸,多買點吃的。
可是這個光芒燦爛的情景轉瞬即逝,壹雙粗魯的手強行脫去他的鐵路制服,把已經走到死亡邊緣的他暫時呼喚了回來。他感到身體已經麻木,殘存的意識讓他知道那個流浪漢正在幹什麽,流浪漢脫下自己破舊的藍色衣服,穿上他嶄新的鐵路制服。他微弱地說,求求妳。流浪漢聽到他的聲音,俯下身體。他說,兩百元。流浪漢摸了摸他的襯衣口袋,從裏面摸出兩百元,放進剛剛屬於自己的鐵路制服的口袋。他再次微弱地說,求求妳。流浪漢再次聽到他的哀求,站在那裏看了他壹會兒,蹲下去把破舊的藍色衣服給他穿上。
流浪漢聽到他臨終的聲音:“謝謝。”
黑暗無邊無際,他沈沒在萬物消失之中,自己也在消失。然後他好像聽到有人在呼喚“楊飛”,他的身體站立起來,站起來時發現自己行走在空曠孤寂的原野上,呼喚“楊飛”的正是他自己。他繼續行走繼續呼喚,楊飛、楊飛、楊飛、楊飛、楊飛、楊飛、楊飛……只是聲音越來越低。他在原野上走了很長的路,不知道走了壹天,還是走了幾天,他對我名字的持續呼喚,讓他來到自己的城市。他的“楊飛”的呼喚聲像路標那樣,引導他來到我們的小店鋪,他在店鋪前的街道對面佇立很久,不知道是幾天還是十幾天,店鋪的門窗壹直關閉,我壹直沒有出現。
他佇立在那裏,四周熟悉的景象逐漸陌生起來,街道上來往的行人和車輛開始模糊不清,他隱約感到自己佇立的地方正在變得虛無縹緲。可是店鋪壹直是清晰的,他也就壹直站在那裏,期待店鋪的門窗打開,我從裏面走出來。店鋪的門窗終於打開了,他看見壹個女人從裏面走出來,轉身和店鋪裏的壹個男人說話。他看清楚了,店鋪裏的男人不是我,他失落地低下頭,轉身離去。
“楊飛把店鋪賣了,去找妳了。”李月珍告訴他。
他點點頭說:“我看見走出來的是別人,知道楊飛把店鋪賣了。”
後來他壹直在走,壹直在迷路,持續不斷的迷路讓他聽到夜鶯般的歌聲。他跟隨著歌聲走去,見到很多骨骼的人在走來走去,他穿梭其間,在夜鶯般的歌聲引導下走進壹片樹林,樹葉越來越寬大,壹些寬大的樹葉上躺著晃晃悠悠的嬰兒,夜鶯般的歌聲就是從這裏飄揚起來的。壹個穿著白色衣服的女人從樹木和草叢裏走了過來,他認出是李月珍。李月珍也認出他,那時候他們兩個都還有著完好的形象。他們站在發出夜鶯般歌聲的嬰兒中間,訴說起各自在那個離去世界裏的最後時刻。他向李月珍打聽我,李月珍所知道的最後情景,就是我去了他的村莊,後來的她不知道了。
他太累了,在二十七個嬰兒夜鶯般的歌聲裏躺了幾天,躺在樹葉之下草叢之上。然後他站起來,告訴李月珍他想念我,他太想見上我壹面,即使是遠遠看我壹眼,他也會知足。他重新長途跋涉,在迷路裏不斷迷路,可是他已經不能接近城市,因為他離開那個世界太久了。他日夜行走,最終來到殯儀館,這是兩個世界僅有的接口。
他走進殯儀館的候燒大廳,就像我第壹次走進那裏壹樣,聽著候燒者們談論自己的壽衣、骨灰盒和墓地,看著他們壹個個走進爐子房。他沒有坐下來,壹直站在那裏,然後他覺得候燒大廳應該有壹名工作人員,他是壹個熱愛工作的人。當壹個遲到的候燒者走進來時,他不由自主迎上去為他取號,又引導他坐下。然後他覺得自己很像是那裏的工作人員,他在中間的走道上走來走去。有壹天,他的右手無意中伸進流浪漢給他穿上的破舊藍色衣服的口袋,摸出壹副破舊的白手套,他戴上白手套以後,感到自己儼然已是候燒大廳裏正式的工作人員。日復壹日,他在候燒者面前彬彬有禮行使自己的職責;日復壹日,他滿懷美好的憧憬,知道只要守候在這裏,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他就能見上我壹面。
李月珍的聲音暫停在這裏。我知道父親在哪裏了,殯儀館候燒大廳裏那個身穿藍色衣服戴著白手套的人,那個臉上只有骨頭沒有皮肉的人,那個聲音疲憊而又憂傷的人,就是我的父親。
李月珍的聲音重又響起,她說我父親曾經從殯儀館回到這裏,走到她那裏講述他如何走進殯儀館的候燒大廳,如何在那裏開始自己新的職業,說完他就轉身離去。李月珍說他那麽匆忙,可能是不應該離開那裏。
李月珍說話的聲音像是滴水的聲音,說出的每壹個字都如壹顆落地的水珠。
“楊飛。”
我知道這個聲音會是陌生的,如同李青的聲音是陌生的那樣,但是我能夠從聲調裏分辨出父親的叫聲。在那個離去的世界裏,父親叫我的聲音裏總是帶著親切的聲調,在這個世界裏應該也是這樣。
這裏四處遊蕩著沒有墓地的身影,這些無法抵達安息之地的身影恍若移動的樹木,時而是壹棵壹棵分開的樹,時而是壹片壹片聚集起來的樹林。我行走在他們中間,仿佛行走在被砍伐過的森林裏。我期待父親的聲音出現,在前面、在後面、在左邊、在右邊,我的名字被他喊叫出來。
我不時遇到手臂上戴著黑紗的人,那些被黑紗套住的袖管顯得空空蕩蕩,我知道他們來到這裏很久了,他們的袖管裏已經沒有皮肉,只剩下骨骼。他們和我相視而笑,他們的笑容不是在臉上的表情裏,而是在空洞的眼睛裏,因為他們的臉上沒有表情了,只有石頭似的骨骼,但是我感受到那些會心的微笑,因為我們是同樣的人,在另外壹個世界裏沒有人會為我們戴上黑紗,我們都是在自己悼念自己。
壹個手臂上戴著黑紗的人註意到我尋找的眼神,他站立在我面前,我看著他骨骼的面容,他的前額上有壹個小小洞口,他發出友好的聲音。
“妳在找人?”他問我,“妳是找壹個人,還是找幾個人?”
“找壹個人。”我說,“我的父親,他可能就在這裏。”
“妳的父親?”
“他叫楊金彪。”
“名字在這裏沒有用。”
“他六十多歲……”
“這裏的人看不出年齡。”
我看著在遠處和近處走動的骨骼,確實看不出他們的年齡。我的眼睛只能區分高的和矮的,寬的和細的;我的耳朵只能區分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小的。
我想到父親最後虛弱不堪的模樣,我說:“他身高壹米七,很瘦的樣子……”
“這裏的人都是很瘦的樣子。”
我看著那些瘦到只剩下骨骼的人,不知道如何描述我的父親了。
他問我:“妳記得他是穿什麽衣服過來的?”
“鐵路制服,”我告訴他,“嶄新的鐵路制服。”
“他過來多久了?”
“壹年多了。”
“我見過穿其他制服的,沒見過穿鐵路制服的。”
“也許別人見過穿鐵路制服的。”
“我在這裏很久了,我沒見過,別人也不會見過。”
“也許他換了衣服。”
“不少人是換了衣服來到這裏的。”
“我覺得他就在這裏。”
“妳要是找不到他,他可能去墓地了。”
“他沒有墓地。”
“沒有墓地,他應該還在這裏。”
我在尋找父親的遊走裏不知不覺來到那兩個下棋的骨骼跟前,他們兩個盤腿坐在草地上,像是兩個雕像那樣專註。他們的身體紋絲不動,只是手在不停地做出下棋的動作。我沒有看見棋盤,也沒有看見棋子,只看見他們骨骼的手在下棋,我看不懂他們是在下象棋,還是在下圍棋。
壹只骨骼的手剛剛放下壹顆棋子,馬上又拿了起來,兩只骨骼的手立刻按住這只骨骼的手。兩只手的主人叫了起來:
“不能悔棋。”
壹只手的主人也叫了起來:“妳剛才也悔棋了。”
“我剛才悔棋是因為妳前面悔棋了。”
“我前面悔棋是因為妳再前面悔棋了。”
“我再前面悔棋是因為妳昨天悔棋了。”
“昨天是妳先悔棋,我再悔棋的。”
“前天先悔棋的是妳。”
“再前天是誰先悔棋?”
兩個人爭吵不休,他們互相指責對方悔棋,而且追根溯源,指責對方悔棋的時間從天數變成月數,又從月數變成年數。
兩只手的主人叫道:“這步棋不能讓妳悔,我馬上要贏了。”
壹只手的主人叫道:“我就要悔棋。”
“我不和妳下棋了。”
“我也不和妳下了。”
“我永遠不和妳下棋了。”
“我早就不想和妳下棋了。”
“我告訴妳,我要走了,我明天就去火化,就去我的墓地。”
“我早就想去火化,早就想去我的墓地了。”
我打斷他們的爭吵:“我知道妳們的故事。”
“這裏的人都知道我們的故事。”壹個說。
“新來的可能不知道。”另壹個糾正道。
“就是新來的不知道,我們的故事也爛大街了。”
“文明用語的話,我們的故事家喻戶曉。”
我說:“我還知道妳們的友情。”
“友情?”
他們兩個發出嘻嘻笑聲。
壹個問另壹個:“友情是什麽東西?”
另壹個回答:“不知道。”
他們兩個嘻嘻笑著擡起頭來,兩雙空洞的眼睛看著我,壹個問我:“妳是新來的?”
我還沒有回答,另壹個說了:“就是那個漂亮妞帶來的。”
兩個骨骼低下頭去,嬉笑著繼續下棋。好像剛才沒有爭吵,剛才誰也沒有悔棋。
他們下了壹會兒,壹個擡頭問我:“妳知道我們在下什麽棋?”
我看了看他們手上的動作說:“象棋。”
“錯啦,是圍棋。”
接著另壹個問我:“現在知道我們下什麽棋了吧?”
“當然,”我說,“是圍棋。”
“錯啦,我們下象棋了。”
然後他們兩個同時問我:“我們現在下什麽棋?”
“不是圍棋,就是象棋。”我說。
“又錯啦。”他們說,“我們下五子棋了。”
他們兩個哈哈大笑,兩個做出同樣的動作,都是壹只手捂住自己肚子的部位,另壹只手搭在對方肩膀的部位。兩個骨骼在那裏笑得不停地抖動,像是兩棵交叉在壹起的枯樹在風中抖動。
笑過之後,兩個骨骼繼續下棋,沒過壹會兒又因為悔棋爭吵起來。我覺得他們下棋就是為了爭吵,兩個妳來我往地指責對方悔棋的歷史。我站在那裏,聆聽他們快樂下棋的歷史和悔棋後快樂爭吵的歷史。他們其樂無窮地指責對方的悔棋劣跡,他們的指責追述到七年前的時候,我沒有耐心了,我知道還有七八年的時間等待他們的追述,我打斷他們。
“妳們誰是張剛?誰是李姓,”我遲疑壹下,覺得用當時報紙上的李姓男子不合適,我說,“誰是李先生?”
“李先生?”
他們兩個互相看看後又嘻嘻笑起來。
然後他們說:“妳自己猜。”
我仔細辨認他們,兩個骨骼似乎壹模壹樣,我說:“我猜不出來,妳們像是雙胞胎。”
“雙胞胎?”
他們兩個再次嘻嘻笑了。然後重新親密無間下起棋來,剛才暴風驟雨似的爭吵被我打斷後立刻煙消雲散。
接著他們故伎重演,問我:“妳知道我們在下什麽棋?”
“象棋,圍棋,五子棋。”我壹口氣全部說了出來。
“錯啦。”他們說,“我們在下跳棋。”
他們再次哈哈大笑,我再次看到他們兩個壹只手捂住自己肚子的部位,另壹只手搭在對方肩膀的部位,兩個骨骼節奏整齊地抖動著。
我也笑了。十多年前,他們兩個相隔半年來到這裏,他們之間的仇恨沒有越過生與死的邊境線,仇恨被阻擋在了那個離去的世界裏。
我尋找父親的行走周而復始,就像鐘表上的指針那樣走了壹圈又壹圈,壹直走不出鐘表。我也壹直找不到父親。
我幾次與壹個骨骼的人群相遇,有幾十個,他們不像其他的骨骼,有時聚集到壹起,有時又分散開去,他們始終圍成壹團行走著。如同水中的月亮,無論波浪如何拉扯,月亮始終圍成壹團蕩漾著。
我第四次與他們相遇時站住腳,他們也站住了,我與他們互相打量。他們的手連接在壹起,他們的身體依靠在壹起,他們組合在壹起像是壹棵茂盛的大樹,不同的樹枝高高低低。我知道他們中間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孩子,我向他們微笑,對他們說:
“妳們好!”
“妳好!”
我聽到他們齊聲回答,有男聲和女聲,有蒼老的聲音和稚嫩的聲音,我看到他們空洞的眼睛裏傳遞出來的笑意。
“妳們有多少人?”我問他們。
他們還是齊聲回答:“三十八個。”
“妳們為什麽總是在壹起?”我繼續問。
“我們是壹起過來的。”男聲回答。
“我們是壹家人。”女聲補充道。
他們中間響起壹個男孩的聲音:“為什麽妳只有壹個人?”
“我不是壹個人。”我低頭看看自己左臂上的黑紗說,“我在尋找我的父親,他穿著鐵路制服。”
我面前的骨骼人群裏有壹個聲音說話了:“我們沒有見過穿鐵路制服的人。”
“他可能是換了衣服來到這裏的。”我說。
壹個小女孩脆生生的聲音響起來:“爸爸,他是新來的嗎?”
所有的男聲說:“是的。”
小女孩繼續問:“媽媽,他是新來的嗎?”
所有的女聲說:“是的。”
我問小女孩:“他們都是妳的爸爸和媽媽?”
“是的。”小女孩說,“我以前只有壹個爸爸壹個媽媽,現在有很多爸爸很多媽媽。”
剛才的男孩問我:“妳是怎麽過來的?”
“好像是壹場火災。”我說。
男孩問身邊的骨骼們:“為什麽他沒有燒焦?”
我感受到了他們沈默的凝視,我解釋道:“我看見火的時候,聽到了爆炸,房屋好像倒塌了。”
“妳是被壓死的嗎?”小女孩問。
“可能是。”
“妳的臉動過了。”男孩說。
“是的。”
小女孩問我:“我們漂亮嗎?”
我尷尬地看著面前站立的三十八個骨骼,不知道如何回答小女孩脆生生的問題。
小女孩說:“這裏的人都說我們越來越漂亮了。”
“是這樣的,”男孩說,“他們說到這裏來的人都是越來越醜,只有我們越來越漂亮。”
我遲疑片刻,只能說:“我不知道。”
壹個老者的聲音在他們中間響了起來:“我們在火災裏燒焦了,來到這裏像是三十八根木炭,後來燒焦的壹片片掉落,露出現在的樣子,所以這裏的人會這麽說。”
這位老者向我講述起他們的經歷,另外三十七個無聲地聽著。我知道他們的來歷了,在我父親不辭而別的那壹天,距離我的小店鋪不到壹公裏的那家大型商場突然起火,銀灰色調的商場燒成了黑乎乎木炭的顏色。市政府說是七人死亡,二十壹人受傷,其中兩人傷勢嚴重。網上有人說死亡人數超過五十,還有人說超過壹百。我看著面前的三十八個骨骼,這些都是被刪除的死亡者,可是他們的親人呢?
我說:“妳們的親人為什麽也要隱瞞?”
“他們受到威脅,也拿到封口費。”老者說,“我們已經死了,只要活著的親人們能夠過上平安的生活,我們就滿足了。”
“孩子呢?他們的父母……”
“現在我們是孩子的父母。”老者打斷我的話。
然後他們手牽著手,身體靠著身體從我身旁無聲地走了過去。他們圍成壹團走去,狂風也不能吹散他們。
我遠遠看見兩個肉體完好的人從壹片枝繁葉茂的桑樹林那邊走了過來。這是衣著簡單的壹男壹女,他們身上所剩無幾的布料不像是穿著,像是遮蔽。他們走近時,我看清了女的身上只有黑色的內褲和胸罩,男的只有藍色的內褲。女的壹副驚魂未定的表情,蜷縮著身體走來,雙手放在大腿上,仿佛在遮蓋大腿。男的彎腰摟住她走來,那是保護的姿態。
他們走到我面前,仔細看著我,他們的目光像是在尋找記憶裏熟悉的面容。我看見失望的表情在他們兩個的臉上漸漸浮現,他們確定了不認識我。
男的問我:“妳是新來的?”
我點點頭,問他們:“妳們也是新來的,妳們是夫妻?”
他們兩個同時點頭,女的發出可憐的聲音:“妳在那邊見過我們的女兒嗎?”
我搖了搖頭,我說:“那邊人山人海,我不知道哪個是妳們的女兒。”
女的傷心地垂下了頭,男的用手撫摸她的肩膀,安慰她:“還會有新來的。”
女的重復我剛才的話:“可是那邊人山人海。”
男的繼續說:“總會有壹個新來的在那邊見過小敏。”
小敏?我覺得這是壹個曾經聽到過的名字。我問他們:“妳們是怎麽過來的?”
他們臉上掠過絲絲恐懼的神色,這是那個離去世界裏的經歷投射到這裏的陰影。他們的眼睛躲開我的目光,可能是眼淚在躲開我的目光。
然後男的講述起那個可怕的經歷。他們住在盛和路上,市裏要拆除那裏的三幢樓房,那裏的住戶們拒絕搬遷,與前來拆遷的對抗了三個多月,拆遷的在那個可怕的上午實施了強拆行動。他們夫妻兩個下了夜班清晨回家,叫醒女兒,給她做了早餐,女兒背著書包去上學,他們上床入睡。他們在睡夢裏聽到外面擴音器發出的壹聲聲警告,他們太疲倦了,沒有驚醒過來。此前他們聽到過擴音器發出的警告聲,見到過推土機嚴陣以待的架式,可是在與住戶們對峙之後,擴音器和推土機撤退而去。所以他們以為又是來嚇唬的,繼續沈溺在睡夢裏。直到樓房響聲隆隆劇烈搖晃起來,他們才被嚇醒。他們住在樓房的壹層,男的從床上跳起來,拉起女的朝門口跑去,男的已經打開屋門,女的突然轉身跑向沙發去拿衣服,男的跑回去拉女的,樓房轟然倒塌。
男的講述的聲音在這裏戛然而止,女的哭泣之聲響起了。
“對不起,對不起……”
“不要說對不起。”
“我不該拿衣服……”
“來不及了,妳就是不拿衣服也來不及了。”
“我不拿衣服,妳就不會跑回來,妳就能逃出去。”
“我逃出去了,妳怎麽辦?”
“妳逃出去了,小敏還有父親。”
我知道他們的女兒是誰了,就是那個穿著紅色羽絨服坐在鋼筋水泥的廢墟上,在寒風裏做作業等待父母回來的小女孩。
我告訴他們:“我見到過妳們的女兒,她叫鄭小敏。”
他們兩個同時叫了起來:“是的,是叫鄭小敏。”
我說:“她念小學四年級。”
“是的,”他們急切地問,“妳怎麽知道的?”
我對男的說:“我們通過電話,我是來做家教的那個。”
“妳是楊老師?”
“對,我是楊飛。”
男的對女的說:“他就是楊老師,我說我們收入不多,他馬上答應每小時只收三十元。”
女的說:“謝謝妳。”
在這裏聽到感謝之聲,我苦笑了。
男的問我:“妳怎麽也過來了?”
我說:“我坐在壹家餐館裏,廚房起火後爆炸了。我和妳們同壹天過來的,比妳們晚幾個小時。我在餐館裏給妳手機打過電話,妳沒有接聽。”
“我沒有聽到手機響。”
“妳那時候在廢墟下面。”
“是的,”男的看著女的說,“手機可能被壓壞了。”
女的急切地問:“小敏怎麽樣了?”
“我們約好下午四點到妳們家,我到的時候那三幢樓房沒有了……”
我猶豫之後,沒有說他們兩個在盛和路強拆事件中的死亡被掩蓋了。我想,壹個他們夫妻兩人同時因公殉職的故事已經被編造出來,他們的女兒會得到兩個裝著別人骨灰的骨灰盒,然後在壹個美麗的謊言裏成長起來。
“小敏怎麽樣了?”女的再次問。
“她很好,”我說,“她是我見過的最懂事的孩子,妳們可以放心,她會照顧好自己的。”
“她只有十壹歲。”女的心酸地說,“她每次出門上學,走過去後都會站住腳,喊叫爸爸和媽媽,等我們答應了,她說壹聲‘我走了’,再等我們答應了,她才會去學校。”
“她和妳說了什麽?”男的問。
我想起了在寒風裏問她冷不冷,她說很冷,我讓她去不遠處的肯德基做作業,我說那裏暖和,她搖搖頭,說爸爸媽媽回來會找不到她的。她不知道父母就在下面的廢墟裏。
我再次猶豫後,還是把這些告訴了他們,最後說:“她就坐在妳們上面。”
我看見淚水在他們兩個的臉上無聲地流淌,我知道這是不會枯竭的淚水。我的眼睛也濕潤了,趕緊轉身離去,走出壹段路程後,身後的哭聲像潮水那樣追趕過來,他們兩個人哭出了人群的哭聲。我仿佛看見潮水把身穿紅色羽絨服的小女孩沖上沙灘,潮水退去之後,她獨自擱淺在那邊的人世間。
我看到了這裏的盛宴。在壹片芳草地上,有碩果累累的果樹,有欣欣向榮的蔬菜,還有潺潺流動的河水。死者分別圍坐在草地上,仿佛圍坐在壹桌壹桌的酒席旁,他們的動作千姿百態,有埋頭快吃的,有慢慢品嘗的,有說話聊天的,有抽煙喝酒的,有舉手幹杯的,有吃飽後摸起了肚子的……我看見幾個肉體的人和幾個骨骼的人穿梭其間,他們做出來的是端盤子的動作和斟酒的動作,我知道這幾個是服務員。
我走了過去,壹個骨骼的人迎上來說:“歡迎光臨譚家菜。”
這個少女般的聲音說出來的譚家菜讓我壹怔,然後我聽到壹個陌生的聲音喊叫我的名字。
“楊飛。”
我沿著聲音望去,看到譚家鑫壹瘸壹拐地快步走了過來,他的右手是托著壹個盤子的動作。我看見了他臉上的喜悅表情,這是在那個離去的世界裏沒有見過的表情,在那裏他面對我的時候只有苦笑。他走到我跟前,欣喜地說:
“楊飛,妳是哪天到這裏的?”
“昨天。”我說。
“我們過來四天了。”
譚家鑫說話時,右手壹直是托著盤子的動作。他回頭喊叫他的妻子和女兒,還有女婿。他大聲喊叫他們的名字,把自己的喜悅傳遞給他們:
“楊飛來啦。”
我見到譚家鑫的妻子、女兒和女婿走來了,他們的手都是端著盤子和提著酒瓶的動作。譚家鑫對著走來的他們說:
“譚家菜今天開張,楊飛今天就來了。”
他們走到我跟前,笑呵呵地上下打量我。譚家鑫的妻子說:“妳看上去瘦了壹些。”
“我們也瘦了。”譚家鑫快樂地說,“來到這裏的人都會越來越瘦,這裏的人個個都是好身材。”
譚家鑫的女兒問我:“妳怎麽也到這裏來了?”
“我沒有墓地。”我說,“妳們呢?”
譚家鑫的臉上掠過壹絲哀愁,他說:“我們的親戚都在廣東,他們可能還不知道我們的事。”
譚家鑫的妻子說:“我們壹家人在壹起。”
快樂的表情回到了譚家鑫的臉上,他說:“對,我們壹家人在壹起。”
我問譚家鑫:“妳的腿斷了?”
譚家鑫笑聲朗朗地說:“腿斷了我走路更快。”
這時那邊響起了叫聲:“我們的菜呢,我們的酒呢……”
譚家鑫轉身對那邊喊叫壹聲:“來啦。”
譚家鑫右手是托著盤子的動作,壹瘸壹拐地快步走去。他的妻子、女兒和女婿是端著盤子提著酒瓶的動作,他們向著那邊急匆匆地走去。
譚家鑫走去時回頭問我:“吃什麽?”
“還是那碗面條。”
“好咧。”
我尋找到壹個座位,坐在草地上,感覺像是坐在椅子上。我的對面坐著壹個骨骼,他做出來的只有飲酒的動作,沒有用筷子夾菜吃飯的動作,他空洞的眼睛望著我手臂上的黑紗。
我覺得他的穿著奇怪,黑色的衣服看上去很寬大,可是沒有袖管,暴露出了骨骼的手臂和肩膀,黝黑的顏色仿佛經歷長年累月的風吹日曬。黑衣在兩側肩膀處留下了毛邊,兩只袖管好像是被撕下的。
我們互相看著,他先說話了:“哪天過來的?”
“第五天了,”我說,“到這裏是昨天。”
他舉起酒杯壹飲而盡,放下酒杯後是斟酒的動作。
他感嘆道:“孤零零壹個人。”
我低頭看看自己手臂上的黑紗。
“妳還知道給自己戴上黑紗過來,”他說,“有些孤零零的冒失鬼來到這裏,沒戴黑紗,看見別人戴著黑紗,就羨慕上了,就來纏著我,要我撕給他們壹截袖管當作黑紗。”
我看著他暴露在外的骨骼的手臂和肩膀,微微笑了起來。他做出了舉杯壹飲而盡和放下酒杯的動作。
他用手比劃著說:“原來的袖管很長,都超過手指,現在妳看看,兩個肩膀都露出來了。”
“妳呢,”我問他,“妳不需要黑紗?”
“我在那邊還有家人,”他說,“他們可能忘掉我了。”
他做出拿起酒瓶的動作和給酒杯斟酒的動作,動作顯示是最後壹杯了,他再次做出壹飲而盡的動作。
“好酒。”他說。
“妳喝的是什麽酒?”我問他。
“黃酒。”他說。
“什麽牌子的黃酒?”
“不知道。”
我笑了,問他:“妳過來多久了?”
“忘了。”
“忘了的話,應該很久了。”
“太久了。”
“妳在這裏應該見多識廣,我請教壹個問題。”我說出了思緒裏突然出現的念頭,“我怎麽覺得死後反而是永生。”
他空洞的眼睛看著我沒有說話。
我說:“為什麽死後要去安息之地?”
他似乎笑了,他說:“不知道。”
我說:“我不明白為什麽要把自己燒成壹小盒灰?”
他說:“這個是規矩。”
我問他:“有墓地的得到安息,沒墓地的得到永生,妳說哪個更好?”
他回答:“不知道。”
然後他扭頭喊叫:“服務員,埋單。”
壹個骨骼的女服務員走過來說:“五十元。”
他做出了將五十元放在桌子上的動作,對我點點頭後起身,離去時對我說:
“小子,別想那麽多。”
我看著他身上寬大的黑色衣服和兩條纖細的骨骼手臂,不由想到甲殼蟲。他的背影逐漸遠去,消失在其他骨骼之中。
譚家鑫的女婿走過來,雙手是端著壹碗面條的動作,隨後是遞給我的動作,我的雙手是接過來的動作。
我做出把那碗面條放在草地上的動作,感覺像是放在桌子上。然後我的左手是端著碗的動作,右手是拿著筷子的動作,我完成了吃壹口面條的動作,我的嘴裏開始了品嘗的動作。我覺得和那個已經離去世界裏的味道壹樣。
我意識到四周充滿歡聲笑語,他們都在快樂地吃著喝著,同時快樂地數落起了那個離去世界裏的毒大米、毒奶粉、毒饅頭、假雞蛋、皮革奶、石膏面條、化學火鍋、大便臭豆腐、蘇丹紅、地溝油。
在朗朗笑聲裏,他們贊美起了這裏的飲食,我聽到新鮮美味健康這樣的詞匯接踵而來。
壹個聲音說:“全中國只有兩個地方的食品是安全的。”
“哪兩個地方?”
“這裏是壹個。”
“還有壹個呢?”
“還有壹個就是那邊的國宴。”
“說得好,”有人說,“我們在這裏享受的是國宴的吃喝待遇。”
我微笑時發現自己吃面條的動作沒有了,我意識到已經吃完,這時聽到旁邊有人喊叫:
“埋單。”
壹個骨骼的服務員走過來,對他說:“八十七元。”
他對服務員說:“給妳壹百。”
服務員說:“找妳十三元。”
他說:“謝啦。”
整個結賬過程只是對話,動作也沒有。這時譚家鑫壹瘸壹拐向我走過來,他手裏是端著壹個盤子的動作,我知道是送給我壹個果盤,我做出接過來的動作。他在我對面坐下來,對我說:
“這是剛剛摘下來的新鮮水果。”
我開始了吃水果的動作,我感覺到了甘美香甜,我說:“譚家菜這麽快又開張了。”
“這裏沒有公安、消防、衛生、工商、稅務這些部門。”他說,“在那邊開壹家餐館,消防會拖上妳壹兩年,說妳的餐館有火災隱患;衛生會拖上妳壹兩年,說妳衛生條件不合格。妳只有給他們送錢送禮了,他們才允許妳開業。”
隨即他有些不安地問我:“妳沒有恨我們吧?”
“為什麽要恨妳們?”
“我們把妳堵在屋子裏。”
我想起在那個世界裏的最後情景,譚家鑫的眼睛在煙霧裏瞪著我,對我大聲喊叫。
我說:“妳好像在對我喊叫。”
“我叫妳快跑。”他嘆了壹口氣說,“我們誰也沒有堵住,就堵住了妳。”
我搖搖頭說:“不是妳們堵住我,是我自己沒有走。”
我沒有告訴他那張報紙和報紙上關於李青自殺的報道,這個說起來過於漫長。
也許以後的某壹個時刻,我會向他娓娓道來。
譚家鑫仍然在內疚裏不能自拔,他向我解釋為何在廚房起火後,他們要堵住大門讓顧客付錢後再走,他說他的飯館經營上入不敷出三年多了。
“我昏了頭。”他說,“害了自己,害了家人,也害了妳。”
“來到這裏也不錯,”我說,“我父親也在這裏。”
“妳父親在這裏?”譚家鑫叫了起來,“他怎麽沒有壹起來?”
“我還沒有找到他。”我說,“我覺得他就在這裏。”
“妳找到後,壹定要帶他過來。”譚家鑫說。
“我會帶他過來的。”我說。
譚家鑫在我對面坐了壹會兒,他不再是愁眉不展,而是笑容滿面。他起身離開時再次說,找到父親後壹定要帶他到這裏來嘗壹嘗。
然後我結賬了,壹個骨骼的女聲走過來,我想她是譚家鑫剛剛招收來的服務員。她對我說:
“面條十壹元,果盤是贈送的。”
我說:“給妳二十元。”
她說:“找妳九元。”
我們之間也是只有對話,沒有動作。當我起身走去時,這個骨骼的女聲在後面熱情地說:
“謝謝光臨!歡迎下次再來!”
在壹片青翠欲滴的竹林前,壹個袖管上戴著黑紗的骨骼走到我面前。我註意到他前額上的小小圓洞,我見過他,向他打聽過父親的行蹤。我向他微笑,他也在微笑,他的微笑不是波動的表情,而像輕風壹樣從他空洞的眼睛和空洞的嘴裏吹拂出來。
“那裏有篝火。”他說,“就在那裏。”
我順著他的手指望向天邊似的望向遠處。遠處的草地正在寬廣地鋪展過去,草地結束的地方有閃閃發亮的跡象,像是壹根絲帶,我感到那是河流。那裏還有綠色的火,看上去像是打火機打出來的微小之火。我看見壹些骨骼的人從山坡走下去,從樹林走出來,陸續走向那裏。
“過去坐壹會兒吧。”他說。
“那是什麽地方?”我問他。
“河邊,”他說,“有壹堆篝火。”
“妳們經常去那裏?”
“不是經常,每隔壹段時間去壹次。”
“這裏的人都去?”
“不是,”他看看我袖管上的黑紗,又指指自己袖管上的黑紗說,“是我們這樣的人。”
我明白了,那裏是自我悼念者的聚集之地。我點點頭,跟隨他走向絲帶般的河流和微小的篝火。我們的腳步在草叢裏延伸過去,青草發出了噝噝響聲。
我看著他袖管上的黑紗,問他:“妳是怎麽過來的?”
“快九年了。”他說。
他的聲音裏出現了追憶的調子:“那時候我結婚兩年多,我老婆有精神病,結婚前我不知道,只和她見過三次,覺得她笑起來有些奇怪,我心裏不踏實,我父母覺得沒什麽,女方的家境很好,嫁妝很多,嫁妝裏還有壹張兩萬元的存折。我們那邊的農村很窮,找對象結婚都是父母做主,兩萬元可以蓋壹幢兩層的樓房,我父母就定下這門親事,結婚後知道她有精神病。
“她還好,不打不鬧,就是壹天到晚嘿嘿笑個不停,什麽活兒都不幹。我父母後悔了,覺得對不起我,但是他們不讓我離婚,說樓房蓋起來了,用的是她嫁妝的錢,不能過河拆橋。我也沒想到要離婚,我想就這樣過下去吧,再說她在精神病裏面算是文靜的,晚上睡著了和正常人沒什麽兩樣。
“那年的夏天,她離家出走,她自己也不知道走到什麽地方。我出去找她,我父母和哥哥嫂子也出去找她,去了很多地方,到處打聽她,沒有她的消息。我們找了三天,找不到她,就去告訴她娘家的人,她娘家的人懷疑是我把她害死的,就去縣裏公安局報案。
“她出走的第五天,離我們村兩公裏遠的地方有壹個池塘裏浮起來壹具女屍,夏天太熱,女屍被發現時已經腐爛,認不出樣子,警察讓我和她娘家的人去辨認,我們都認不出來,只是覺得女屍的身高和她差不多。警察說女屍淹死和她出走是同壹天,我覺得就是她,她娘家的人也覺得就是她。我想她可能是不小心走進池塘裏去的,她有精神病,不知道走進池塘會淹死的。我心裏還是有點難過,不管怎樣我們做了兩年多的夫妻。
“過了兩天,警察來問我,她出走那天我在做什麽,那天我進城了,我是晚上回家發現她不在的。警察問有沒有人可以證明我進城了,我想了想說沒有,警察給我做了筆錄就走了。她娘家的人認定是我殺了她,警察也這麽認為,就把我抓了起來。
“我父母和哥哥嫂子開始不相信我會殺她,後來我自己承認殺了她,他們就相信了。他們很傷心,也怨恨我,我讓他們做人都擡不起頭來,我們那邊的農村就是這樣,家裏出了個殺人犯,全家人都不敢見人。法庭宣判我死刑時他們壹個都沒有來,她娘家的人都來了。我不怪他們,我被抓起來後,他們想來見我,警察不讓他們見,他們都是老實巴交的人,不知道我是冤枉的。
“我承認殺了她是沒有辦法,警察把我吊起來打,逼我認罪,屎尿都被他們打出來了,我的兩只手被捆綁起來吊了兩天,因為失血有四根手指黑了,他們說是壞死了。以後他們就把我反吊起來打,兩只腳吊在上面,頭朝下,反吊起來打最疼的不是身上了,是眼睛,汗水是鹹的,流進眼睛跟針在紮著眼睛那麽疼。我想想還是死了好,就承認了。”
他停頓了壹下問我:“為什麽眉毛要長在眼睛上面?”
“為什麽?”
“為了擋汗水。”
我聽到他的輕輕笑聲,像是獨自的微笑。
他指指自己的後腦,又指指自己前額上的圓洞說:“子彈從後面打進去,從這裏出來的。”
他低頭看看自己袖管上的黑紗,繼續說:“我來到這裏,看見有人給自己戴著黑紗,也想給自己戴,我覺得那邊沒有人給我戴黑紗,我的父母和哥哥嫂子不敢戴,因為我是殺人犯。我看見壹個人,穿著很長很寬的黑衣服,袖管很長,我問他能不能撕下壹截袖管給我,他知道我要它幹什麽,就撕下來壹截送給我。我戴上黑紗後心裏踏實了。
“在我後面過來的人裏邊,有壹個知道我的事,他告訴我,我被槍斃半年後,我的精神病老婆突然回家了,她衣服又臟又破,臉上也臟得沒人能認出來,她站在家門口嘿嘿笑個不停,站了半天,村裏有人認出了她。
“那邊的人終於知道我是冤枉的,我父母和哥哥嫂子哭了兩天,覺得我太可憐了,政府賠償給他們五十多萬,他們給我買了壹塊很好的墓地……”
“妳有墓地?”我問他,“為什麽還在這裏?”
“我那時候把黑紗取下來,扔在壹棵樹下,準備去了,走出了十多步,舍不得,又回去撿起來戴上。”他說,“戴上黑紗,我就不去了。”
“妳不想去安息了?”我問。
“我想去,”他說,“我那時候想反正有墓地了,不用急,什麽時候想去了就去。”
“多少年了?”
“八年了。”
“墓地還在嗎?”
“還在,壹直在。”
“妳打算什麽時候去?”
“以後去。”
我們走到了自我悼念者的聚集之地。我的眼前出現寬闊的河流,閃閃發亮的景象也寬闊起來。壹堆綠色篝火在河邊熊熊燃燒,跳躍不止的綠色火星仿佛是飛舞的螢火蟲。
已經有不少戴著黑紗的骨骼坐在篝火旁,我跟著他走了進去,尋找可以坐下的位置,我看到壹些坐下的骨骼正在移動,為我們騰出壹個又壹個空間,我站在那裏猶豫不決,不知道應該走向哪個。看到他走到近旁的位置坐下,我也走過去坐下來。我擡起頭來,看見還有正在走來的,有的沿著草坡走來,有的沿著河邊走來,他們像涓涓細流那樣匯集過來。
我聽到身旁的骨骼發出友好的聲音:“妳好。”
“妳好”形成輕微的聲浪,從我這裏出發,圍繞著篝火轉了壹圈,回到我這裏後掉落下去。
我悄聲問他:“他們是在問候我嗎?”
“是的,”他說,“妳是新來的。”
我感到自己像是壹棵回到森林的樹,壹滴回到河流的水,壹粒回到泥土的塵埃。
戴著黑紗的陸續坐了下來,仿佛是聲音陸續降落到安靜裏。我們圍坐在篝火旁,寬廣的沈默裏暗暗湧動千言萬語,那是很多的卑微人生在自我訴說。每壹個在那個離去的世界裏都有著不願回首的辛酸事,每壹個都是那裏的孤苦伶仃者。我們自己悼念自己聚集到壹起,可是當我們圍坐在綠色的篝火四周之時,我們不再孤苦伶仃。
沒有說話,沒有動作,只有無聲的相視而笑。我們坐在靜默裏,不是為了別的什麽,只是為了感受我們不是壹個,而是壹群。
我在靜默的圍坐裏聽到火的聲音,是舞動聲;聽到水的聲音,是敲擊聲;聽到草的聲音,是搖曳聲;聽到樹的聲音,是呼喚聲;聽到風的聲音,是沙沙聲;聽到雲的聲音,是漂浮聲。
這些聲音仿佛是在向我們傾訴,它們也是命運多舛,它們也是不願回首。然後,我聽到夜鶯般的歌聲飛來了,飛過來壹段,停頓壹下,又飛過來壹段……
我聽到壹個耳語般的聲音:“妳來了。”
我走向這個陌生的聲音,像是雨水從屋檐滴到窗臺上的聲音,清晰和輕微。我判斷出這是壹個女人的聲音,飽經風霜之後,聲音裏有著黃昏時刻的暗淡,可是仍然節奏分明,像是有人在敲門,壹下,兩下,三下。
“妳來了。”
我有些疑惑,這個聲音是不是在對我說?可是聲音裏有著遙遠的親切,記憶深處的那種親切,讓我覺得聲音就是在對我說,說了壹遍又壹遍。接著我又聽到了夜鶯般的歌聲,波浪壹樣蕩漾過來。“妳來了”的聲音踏著夜鶯般的歌聲向我而來。
我走向夜鶯般的歌聲和“妳來了”的聲音。
我走進壹片樹林,感到夜鶯般的歌聲是從前面的樹上滑翔下來的。我走過去,註意到樹葉越來越寬大,然後我看見壹片片寬大搖曳的樹葉上躺著只剩下骨骼的嬰兒,他們在樹葉的搖籃裏晃晃悠悠,唱著動人魂魄的歌聲。我伸出手指,壹個個數過去,數到二十七個以後沒有了,我放下手。這個數字讓我心裏為之壹動,我的記憶瞬間追趕上那個離去的世界,我想起漂浮在河水裏和丟棄在河岸邊的二十七個被稱為醫療垃圾的死嬰。
“妳來了。”
我看見壹個身穿寬大白色衣服的骨骼坐在樹木之間芳草叢中,她慢慢站了起來,嘆息壹聲,對我說:
“兒子,妳怎麽這麽快就來了?”
我知道她是誰了,輕輕叫了壹聲:“媽媽。”
李月珍走到我跟前,空洞的眼睛凝視我,她的聲音飄忽不定,她說:“妳看上去有五十多歲了,可是妳只有四十壹歲。”
“妳還記得我的年齡。”我說。
“妳和郝霞同齡。”她說。
此刻郝霞和郝強生在另壹個世界裏的美國,我和李月珍在這個世界裏的這裏。郝霞和郝強生離開時,我送他們到機場,他們飛到上海後再轉機去美國。我請求郝強生,讓我來捧著骨灰盒,我要送這位心裏的母親最後壹程。
“我看見妳們去了機場,看見妳捧著骨灰盒。”李月珍說著搖了搖頭,“不是我的骨灰,是別人的。”
我想到別人的骨灰以她的名義安葬在了美國,我告訴她:“郝霞說已經給妳找好安息之地,說以後爸爸也在那裏。”
我沒有說下去,因為我想到多年後郝強生入土時,不會和李月珍共同安息,他將和壹個或者幾個殘缺不全的陌生者共處壹隅。
李月珍空洞的眼睛裏滴出了淚珠,她也想到這個。淚珠沿著她石頭似的臉頰流淌下去,滴落在幾根青草上。然後她空洞的眼睛裏出現笑意,她擡頭看看四周夜鶯壹樣歌唱的嬰兒,她說:
“我在這裏有二十七個孩子,現在妳來了,我就有二十八個了。”
她只剩下骨骼的手指撫摸起了我左臂上的黑布,她知道我是在悼念自己,她說:
“可憐的兒子。”
我冰冷的心裏出現了火焰跳躍般的灼熱。有壹個嬰兒不小心從樹葉上滾落下來,他吱吱哭泣著爬到李月珍跟前,李月珍把他抱到懷裏輕輕搖晃了壹會兒,再把他放回到寬大的樹葉上,這個嬰兒立刻快樂地加入到其他嬰兒夜鶯般的歌唱裏去了。
“妳是怎麽過來的?”李月珍問我。
我把自己在那邊的最後情景告訴了她,還說了李青千裏迢迢來向我告別。
她聽後嘆息壹聲說:“李青不應該離開妳。”
也許是吧,我心想。如果李青當初沒有離開我,我們應該還在那個世界裏過著平靜的生活,我們的孩子應該上小學了,可能是壹個中學生。
我想起李月珍和二十七個死嬰的神秘失蹤,殯儀館聲稱已經將她和二十七個死嬰火化了,網上有人說她和二十七個死嬰的骨灰是從別人的骨灰盒裏分配出來的。
“我知道這些,”她說,“後面過來的人告訴我的。”
我擡頭看看躺在寬大樹葉上發出夜鶯般歌聲的嬰兒們,我說:“妳把他們抱到這裏?”
“我沒有抱他們,”她說,“我走在前面,他們在後面爬著。”
李月珍說那天深夜沒有聽到轟然響起的塌陷聲,但是她醒來了。此前她沈溺在三個沈睡裏,她在第壹個沈睡裏見到遼闊的混沌,天和地渾然壹體,壹道光芒像地平線那樣出現,然後光芒潮水似的湧來,天和地分開了,早晨和晚上也分開了;在第二個沈睡裏見到空氣來了,快速飛翔和穿梭;在第三個沈睡裏見到水從地上蔓延開來,越來越像大海。
然後她醒來了,身體似乎正從懸崖掉落,下墜的速度讓她的身體豎立起來,她慢慢扯開那塊白布,像是清除堵在門前的白雪,她的雙腳開始走動,走出天坑底下的太平間,冷清的月光灑滿天坑,她的雙腳踩到犬牙交錯似的坑壁,以躺著的姿態走出天坑。
她走在被燈光照亮的城市裏,行人車輛熙熙攘攘,景物依舊,可是她的行走置身其外。
她像是回家那樣自然而然走到自己居住的樓房前,可是她不能像回家那樣走進去,無論她的雙腿如何擺動,也無法接近那幢樓房,那是她離開人世的第三個夜晚。她看見六樓的窗口閃過壹個女人的身影,心裏怦然而動,那是郝霞,女兒回來了。
接下去的兩個晝夜裏,她沒有停止自己向前的步伐,可是漸行漸遠。那個窗口壹直沒有出現郝強生,也沒有出現我,郝霞也只是出現壹次。她看見陸續有人搬著桌子椅子櫃子,搬著茶幾沙發,搬著床從樓房裏出來,她知道這些與她朝夕相處幾十年的家具賣掉了,那套房子也賣掉了,她的丈夫和女兒即將飛往美國。
她終於看見我們,在下午的時刻,郝強生捧著骨灰盒在郝霞的攙扶下走出樓房,郝霞右手還提著壹只很大的行李袋,我提著兩個很大的行李箱跟在後面,我們三個站在路邊,壹輛出租車停下,我和司機壹起把兩個行李箱和郝霞手裏的行李袋放進後備箱。她看見我對郝強生說了幾句話,郝強生把骨灰盒交給我,我捧起骨灰盒,郝霞與郝強生坐進後座,我坐進前座,出租車駛去了。
她知道這是永別的時刻,郝強生和郝霞要去遙遠的美國,她潸然淚下,身體奔跑起來,可是奔跑仍然讓她遠離我們,她站住了,看著出租車消失在街上的車流裏。
她哭出了聲音,哭了很久後聽到身後有噝噝的聲響,仿佛也是哭泣之聲,她回頭看見二十七個嬰兒排成壹隊匍匐在地,他們似乎和她壹樣傷心。當她的哭泣停止後,他們噝噝的哭聲也停止了。她不知道他們跟在她的後面爬出天坑,又壹直跟著她爬到這裏。她看著前面漸漸遠去的城市,又回頭看看二十七個嬰兒,知道自己失去了什麽,又得到了什麽。
她輕聲對嬰兒們說:“走吧。”
身穿白色衣褲的李月珍緩步前行,二十七個嬰兒排成壹隊在她後面爬行。陽光是陳舊的黃色,他們穿過鬧哄哄的城市,走進寧靜之中,迎來銀灰色的月光,他們在寧靜裏越走越深。
越過生與死的邊境線之後,李月珍踏上壹片芳草地,青青芳草摩擦了後面爬行的二十七個嬰兒的脖子,癢癢的感覺讓二十七個嬰兒發出咯吱的笑聲。芳草地結束之後是壹條閃閃發亮的河流,李月珍走入河水,河水慢慢上升到她的胸口,又慢慢下降到她的腳下,她來到對岸;二十七個嬰兒在水面上爬行過去,他們嗆到水了,咳嗽的聲音壹直響到對岸。他們過河入林,在樹林裏李月珍不知不覺哼唱起某壹個曲調,後面二十七個嬰兒也哼唱起來。李月珍停止哼唱後,二十七個嬰兒沒有停止,夜鶯般的歌聲壹直響到現在。
“妳父親來過,”李月珍說,“楊金彪來過。”
我吃驚地看著她,她繼續說:“他走了很遠的路來到這裏,他很累,在這裏躺了幾天,壹直在念叨妳。”
“他不辭而別去了哪裏?”
“他上了火車,去了當年丟棄過妳的地方。”
我銘記著與父親最後壹夜的對話。我們擠在小店鋪的狹窄床上,窗外路燈的光亮似乎昏昏欲睡,夜風正在撫摸我們的窗戶。父親第壹次在我面前哭了,他講述我四歲時,為了壹個姑娘把我丟棄在那個陌生城市的壹塊石頭上,他描述那塊青色石頭的粗糲和石頭表面的平滑,他把我放在平滑的上面。他為此指責自己的狠心,壹聲又壹聲。可是父親不辭而別,我沒有想到這個,我去了很多地方找他,卻沒有想到他會坐上火車去了那裏。
我父親穿上嶄新的鐵路制服,這是他最新的制服,壹直舍不得穿,直到離去的時候才穿在身上。他拖著虛弱不堪的身體登上火車,吃力地找到自己的座位,身體剛剛在座位上安頓下來,火車就啟動了。看著站臺緩緩後退而去,他突然感到自己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他不知道這麽壹走是否還能再見到我。
父親告訴李月珍,在那個晚上,他沒有睡著,壹直在聽著我均勻的呼吸聲和時而出現的鼾聲,中間有壹會兒我沒有聲息,他擔心了,伸手摸了我的臉和脖子,我被驚醒,支起身體看著他,他閉上眼睛假裝睡著。他說我在黑暗裏摸了摸他的身體,小心翼翼地把他的胳膊放進被子裏。
我搖搖頭,告訴李月珍:“我不知道這些。”
李月珍指了指身前樹下的草叢說:“他就躺在這裏,壹直在說話。”
我父親找到了那個地方,可是沒有找到那塊青色的石頭和那片樹林,還有那座石板橋和那條沒有河水的小河;他記得石板橋的對面應該有壹幢房屋,房屋裏應該有孩子們唱歌的聲音,他沒有找到那幢房子,沒有聽到孩子們的歌聲。父親告訴李月珍,壹切都變了,連火車也變了。當年他和我乘坐的火車黎明時刻駛出站臺,中午才到達那座小城。後來他獨自壹人乘坐的仍然是黎明時刻出發的火車,可是壹個多小時就到了那裏。
李月珍問他:“妳還記得那個地名?”
“記得,”他說,“河畔街。”
他在早晨的陽光裏走出那個城市的車站,他的身旁都是背著行李袋拖著行李箱快步走去的旅客,他們像沖鋒壹樣。他緩慢移動的身體上空空蕩蕩,沒有行李袋也沒有行李箱,可是他的身體比那些行李袋和行李箱都要沈重。他緩步走向出站口,他的雙手無力下垂,幾乎沒有甩動。
他站在車站前的廣場上,聲音虛弱地詢問從身旁匆忙經過的那些健康身體是不是本地人,他詢問了二十多個,只有四個說自己是本地人,他向他們打聽怎麽去河畔街,前面三個年輕人都不知道河畔街在哪裏,第四個是老人,知道河畔街,告訴他需要換乘三次公交車才能到那裏。他登上壹輛公交車,拖著奄奄壹息的身體,在舉目無親的城市裏尋找起那個遺棄過我的陌生之地。
李月珍問他:“為什麽去那裏?”
他說:“我就想在那塊石頭上坐壹會兒。”
他找到那個地方的時候已是下午。擁擠的公交車讓他筋疲力盡,下了壹輛之後他需要在街邊坐上很長時間,才有力氣登上另壹輛。他輾轉三次公交車,在距離河畔街三百多米的公交車站下車。接下來的三百米路程對於他比三千米還要漫長,他艱難前行,步履沈重,兩只腳仿佛是兩塊石頭壹樣提不起來,只能在人行道上慢慢移動,走上五六米之後,他就要扶住壹棵樹休息片刻。他看到街邊有壹家小吃店,覺得自己應該吃點東西,就在店外人行道上擺著的凳子上坐下來,雙臂擱在桌子上支撐身體,他給自己要了壹碗餛飩。他吃下去三口就嘔吐起來,吐在隨身攜帶的塑料袋裏。坐在旁邊吃著的人壹個個端起飯碗跑進小吃店裏面,他聲音微弱地對他們說了幾聲對不起,接著繼續吃,繼續嘔吐。然後他吃完了,也吐完了,他覺得吃下去的比吐出來的多,身體有壹些力氣了,他搖晃著站起來,搖晃著走向河畔街。
他告訴李月珍:“那地方全是高樓,住了很多人。”
昔日的小河沒有了,昔日的石板橋也沒有了。他聽到孩子們的聲音,不是昔日孩子們歌唱的聲音,而是今日孩子們嬉戲的聲音。他們在壹個兒童遊玩的區域裏坐著滑梯大聲喊叫,孩子們的爺爺奶奶壹邊聊天壹邊看護他們。這裏已是壹個住宅小區,高樓下的小路像是壹條條夾縫,車和人在裏面往來。他打聽小河在哪裏,石板橋在哪裏,住在這裏的人都是從別處搬過來的,他們說沒有小河沒有石板橋,從來都沒有。他問這裏是叫河畔街嗎?他們說是。他又問這裏以前叫河畔街嗎?他們說以前好像也叫河畔街。
“沒有小河了,還叫河畔街?”李月珍問他。
“地名沒有變,其他都變了。”他說。
他用虛弱的聲音繼續向他們打聽這裏有沒有小樹林,樹林的草叢裏還應該有壹塊青色的石頭。有壹個人告訴他,沒有小樹林,草叢倒是有,在小區旁邊的公園裏,草叢裏也有石頭。他問公園有多遠,那人說很近,只有兩百米,可是這兩百米對他來說仍然是壹次艱難的跋涉。
他走到那個公園時已是黃昏,落日的余輝照耀著壹片草地,草地上錯落有致凸顯的幾塊石頭上有著夕陽溫暖的顏色,他在這幾塊石頭裏尋找記憶中的那塊石頭,感到中間那塊有些發青的石頭很像我當初坐在上面的那壹塊。他緩慢地走到那塊石頭旁,想坐在上面,可是身體不聽使喚滑了下去。他只能靠著石頭坐在草地上,那壹刻他感到自己沒有力氣再站起來了。他的頭歪斜在石頭上,無力地看著近處壹個身穿藍色破舊衣服的流浪漢在壹個垃圾桶裏找吃的,流浪漢從桶裏找出壹個可樂瓶,擰開蓋子往自己嘴裏倒進剩下的幾滴可樂。流浪漢舉起的手在張開的嘴巴上搖動幾下,又把可樂瓶扔回垃圾桶,然後轉過身來盯著他。流浪漢的眼睛像鷹眼壹樣看著他,他垂下了眼睛。過了壹會兒,他擡起眼睛看到流浪漢坐在垃圾桶旁的壹把椅子上,流浪漢的目光仍然盯著他,他感覺那目光盯住自己身上嶄新的鐵路制服。
“我看見楊飛了,”他對李月珍說,“就在那塊石頭上。”
這是彌留之際,他沈沒在黑暗裏,像是沈沒在井水裏,四周寂靜無聲。高樓上的燈光熄滅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也熄滅了。隨即突然出現壹片燦爛光芒,當初他丟棄我的情景在光芒裏再現了。他看見四歲的我坐在石頭上,穿著壹身藍白相間的小水手服,這是他決定丟棄我時給我買來的。壹個小水手坐在青色的石頭上,快樂地搖晃著兩條小腿。他悲哀地對我說,我去買點吃的;我快樂地說,爸爸,多買點吃的。
可是這個光芒燦爛的情景轉瞬即逝,壹雙粗魯的手強行脫去他的鐵路制服,把已經走到死亡邊緣的他暫時呼喚了回來。他感到身體已經麻木,殘存的意識讓他知道那個流浪漢正在幹什麽,流浪漢脫下自己破舊的藍色衣服,穿上他嶄新的鐵路制服。他微弱地說,求求妳。流浪漢聽到他的聲音,俯下身體。他說,兩百元。流浪漢摸了摸他的襯衣口袋,從裏面摸出兩百元,放進剛剛屬於自己的鐵路制服的口袋。他再次微弱地說,求求妳。流浪漢再次聽到他的哀求,站在那裏看了他壹會兒,蹲下去把破舊的藍色衣服給他穿上。
流浪漢聽到他臨終的聲音:“謝謝。”
黑暗無邊無際,他沈沒在萬物消失之中,自己也在消失。然後他好像聽到有人在呼喚“楊飛”,他的身體站立起來,站起來時發現自己行走在空曠孤寂的原野上,呼喚“楊飛”的正是他自己。他繼續行走繼續呼喚,楊飛、楊飛、楊飛、楊飛、楊飛、楊飛、楊飛……只是聲音越來越低。他在原野上走了很長的路,不知道走了壹天,還是走了幾天,他對我名字的持續呼喚,讓他來到自己的城市。他的“楊飛”的呼喚聲像路標那樣,引導他來到我們的小店鋪,他在店鋪前的街道對面佇立很久,不知道是幾天還是十幾天,店鋪的門窗壹直關閉,我壹直沒有出現。
他佇立在那裏,四周熟悉的景象逐漸陌生起來,街道上來往的行人和車輛開始模糊不清,他隱約感到自己佇立的地方正在變得虛無縹緲。可是店鋪壹直是清晰的,他也就壹直站在那裏,期待店鋪的門窗打開,我從裏面走出來。店鋪的門窗終於打開了,他看見壹個女人從裏面走出來,轉身和店鋪裏的壹個男人說話。他看清楚了,店鋪裏的男人不是我,他失落地低下頭,轉身離去。
“楊飛把店鋪賣了,去找妳了。”李月珍告訴他。
他點點頭說:“我看見走出來的是別人,知道楊飛把店鋪賣了。”
後來他壹直在走,壹直在迷路,持續不斷的迷路讓他聽到夜鶯般的歌聲。他跟隨著歌聲走去,見到很多骨骼的人在走來走去,他穿梭其間,在夜鶯般的歌聲引導下走進壹片樹林,樹葉越來越寬大,壹些寬大的樹葉上躺著晃晃悠悠的嬰兒,夜鶯般的歌聲就是從這裏飄揚起來的。壹個穿著白色衣服的女人從樹木和草叢裏走了過來,他認出是李月珍。李月珍也認出他,那時候他們兩個都還有著完好的形象。他們站在發出夜鶯般歌聲的嬰兒中間,訴說起各自在那個離去世界裏的最後時刻。他向李月珍打聽我,李月珍所知道的最後情景,就是我去了他的村莊,後來的她不知道了。
他太累了,在二十七個嬰兒夜鶯般的歌聲裏躺了幾天,躺在樹葉之下草叢之上。然後他站起來,告訴李月珍他想念我,他太想見上我壹面,即使是遠遠看我壹眼,他也會知足。他重新長途跋涉,在迷路裏不斷迷路,可是他已經不能接近城市,因為他離開那個世界太久了。他日夜行走,最終來到殯儀館,這是兩個世界僅有的接口。
他走進殯儀館的候燒大廳,就像我第壹次走進那裏壹樣,聽著候燒者們談論自己的壽衣、骨灰盒和墓地,看著他們壹個個走進爐子房。他沒有坐下來,壹直站在那裏,然後他覺得候燒大廳應該有壹名工作人員,他是壹個熱愛工作的人。當壹個遲到的候燒者走進來時,他不由自主迎上去為他取號,又引導他坐下。然後他覺得自己很像是那裏的工作人員,他在中間的走道上走來走去。有壹天,他的右手無意中伸進流浪漢給他穿上的破舊藍色衣服的口袋,摸出壹副破舊的白手套,他戴上白手套以後,感到自己儼然已是候燒大廳裏正式的工作人員。日復壹日,他在候燒者面前彬彬有禮行使自己的職責;日復壹日,他滿懷美好的憧憬,知道只要守候在這裏,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他就能見上我壹面。
李月珍的聲音暫停在這裏。我知道父親在哪裏了,殯儀館候燒大廳裏那個身穿藍色衣服戴著白手套的人,那個臉上只有骨頭沒有皮肉的人,那個聲音疲憊而又憂傷的人,就是我的父親。
李月珍的聲音重又響起,她說我父親曾經從殯儀館回到這裏,走到她那裏講述他如何走進殯儀館的候燒大廳,如何在那裏開始自己新的職業,說完他就轉身離去。李月珍說他那麽匆忙,可能是不應該離開那裏。
李月珍說話的聲音像是滴水的聲音,說出的每壹個字都如壹顆落地的水珠。